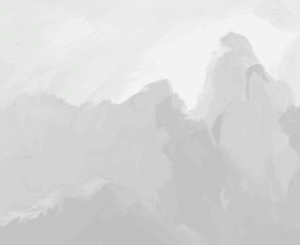1902年2月24日,艾伟德生于英国伦敦以北的埃德蒙顿(Edmonton),父亲是个邮差。因为家境贫寒,故没有受过多少教育,还很年轻时,就到富贵人家做女佣,以维持家庭生计。蒙恩信主后,她热心追求信仰。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中,她在一本宣教杂志上读到一篇关于中国宣教的文章,从中得知在中国尚有几万万人民从未听到过耶稣基督。当时她感到非常惊讶,心里觉得应当为中国人做些什么。从那时起,她就萌生了去中国宣教的意念。大约在27岁时,艾伟德向“中国内地会”提出申请,希望成为一名内地会宣教士,到中国去宣教。但因她既未读过神学,也未上过大学,甚至连中学都未读过,而沒有被接受。“中国内地会”为英国著名宣教士戴德生所创,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宣教团体,对宣教士的要求很高。虽然艾伟德迫切表示:“……好几亿中国人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认识爱我们的神。我知道神要我去中国,我不能不去啊!” 但因她实在不具备宣教士的基本素质——不仅仅文化素质不够,身材也又瘦又小——最终还是被拒了。
但艾伟德毫不气馁,一边继续做女佣,一边攒钱,暗暗为自费去中国做准备。受其赤诚之心所打动,她被介绍去伦敦照顾一对返国养老的宣教士法兰西斯•何斯本(Francis Young Husband)夫妇。何斯本是个作家,写过不少介绍东方的书,在他家里亦有很多藏书。通过与这对夫妇的交谈和阅读,艾伟德学到许多国际知识,特别是关于中国的知识。
1930年初,在参加一次卫理宗教会的聚会中,艾伟德听说有一位在中国山西的老宣教士珍妮•劳森(Jeannie Lawson)已经73岁了,要退休,但因无人接替,一直退不下来,但一时又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艾伟德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立即写信给劳森女士说:“那人就是我。” 几个月后,劳森回信欢迎她去,并且告诉她,只要到达中国天津,就会有人接她到山西阳城,即劳森宣教的地方。
艾伟德在等候回信期间,先去探询旅行去中国的走法。得知从欧洲去遥远的中国有两条路:一是直接坐船到天津,这样走快捷方便,但费用要高得多。另一条路是走陆路,比较经济,但会很艰苦,那就是坐火车东行,经过东欧,再穿越西伯利亚后,进入中国;再转中东铁路南下直到大连,最后由大连坐船到天津。为了省钱,艾伟德选择了第二条路。即便如此,她也几乎花掉了她所有的积蓄。
1930 年10月18日,艾伟德只身踏上了梦寐以求的宣教之路。她随身只带了两个箱子,一个箱子里放有一本圣经和她的衣物,另一个里面装些简单的食物,和一只烧水煮饭的酒精炉;口袋裡的全部盘缠仅有二英镑九便士。前来送行的只有她的父母和姐姐维奥丽(Violet)。她先乘船到荷兰海牙,从那裡登上开往俄国的三等火车。车上没有一个同伴,甚至没有一个懂英语的人可以交谈,她只有在祷告中把一切都交託给神。旅途充满了艰辛与曲折,在西伯利亚,她险些被苏军扣留,后来在素不相识的好心人的帮助下,才得以逃脱,到达苏俄的最东端海参崴;再经日本神户乘船,辗转到达中国天津。那时她已身无分文。
在天津宣教中心等待一些时日后,艾伟德随着一位路姓基督徒商人,坐火车再转汽车到达山西泽州的内地会宣教站。“剑桥七杰”之一司米德的夫人(Mis. Stanley Smith)接待了她,帮助她了解山西的情况,并为她换上了中式旗袍。休息几天之后,艾伟德坐上骡车,再改乘轿子,经过两天的行程,终于到达了阳城。
阳城是一座山中小城,教堂位于城东门外大道上,运货的骡队来来往往,非常热闹。教堂是租来的民居,据当地人说“闹过鬼”,所以租金相当便宜,一年只一英镑。73岁的珍妮•劳森是苏格兰人,已经在中国宣教50年,可说是从风华正茂到风烛残年。艾伟德先将髒乱的房屋、院子打扫干淨,然后协助珍妮,藉闲置的房屋院落开了一间客栈,接待来往的骡夫住宿,取名叫“八福客栈”。“八福”之名取自主耶稣的“登山宝训”中所论及的八种福气。这样,既可将此客栈作为向当地人传福音的据点,也可以接待八方来客,藉他们把福音传向四面八方;而且还可以为宣教筹措些经费。
八福客栈刚办起来时,生意惨淡,根本没人来住宿。因为当地人对“洋鬼子”很仇视,不愿与她们交往。艾伟德只好站在大门口,招徕过往的骡队,想方设法把他们拉进来。刚开始时收效甚微,还经常受到骡夫们的嘲笑,或污言秽语。但渐渐地,也有一些骡夫下车进来看的。当他们看到客栈整洁,饭菜可口,而且收费便宜时,也就动心了。偶而有人住宿后,她们更是竭诚招待,晚上还给旅客们讲圣经故事听。随着日久天长,客栈的人气愈来愈旺,生意也愈来愈好。不久,客栈就常常爆满了。起初,艾伟德以还不流利的中文讲圣经故事给骡夫们听,这些习惯了聚赌喧闹的骡夫们哪有心思听她,还常常取笑她。然而艾伟德不灰心,慢慢地骡夫们受到感召, 一个又一个的信了主。最后骡夫们自己定了公约,客店旅客不准吸烟、饮酒、赌博与喧哗,以免影响艾姑娘说故事。当骡夫们听了福音后,生活发生了明显的改变,不再抽烟、喝酒、赌博;也不再讲髒话,或唱黄色小调,而改唱圣歌了,这事一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当地村民们也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的听圣经故事,渐渐地,各乡镇都有人相信耶稣基督,进而形成教会。以开骡马店、讲故事、唱歌传道的方式宣教,正是艾伟德与众不同的地方。
艾伟德到阳城一年多后,珍妮•劳森不幸去世,“八福客栈”整个担子就落在了29岁的艾伟德身上。此时,泽州的司米德夫人看到她的需要,特地差派一位中国助手来协助她。艾伟德在阳城所做的一切大得人心,影响力渐增,以致有一天阳城的县长也光临八福客栈了。当时官府正在推行“天足运动”,明令妇女放脚,即把缠裹的小脚放开来。县长决定派人挨户检查,以改正多年之陋习。他觉得艾伟德是最合适的人选,并可以现身说法,示范天足的好处,故委派她担当此任,并应许发给她薪水,提供骡子作为交通工具,还派两个卫兵保护她。艾伟德经过考虑,觉得这是神赐给她的机会,就接受了,附带条件是不能限制她传讲福音。就这样,她以官使身份,周游各村镇间,进入家家户户,帮助妇女放脚,也借机把基督福音传给她们,使多人归主。
这样一来,艾伟德在阳城一带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以致于当阳城监狱发生骚乱时,连典狱官都来找她。有一天,阳城监狱的一个囚犯突然发狂,挥刀砍死了好几个同狱中人,狱卒们不敢上前,无人能够制服他。情急之下,典狱官派人找来艾伟德,看她能否藉着神的大能,化解危机。艾伟德壮着胆子,跨过地上的尸首,走近这个杀红了眼的凶徒,用温柔的话劝他放下屠刀,并保证不再加罪。那凶徒竟然垂下头来,将手中的刀交给艾伟德,让狱卒把他押走,一场骚乱就这样平息下来。典狱官非常感激她,此后允许她到狱中向囚犯传福音,并且听从她的建议改善监狱的环境。
艾伟德所做的这些事对当地人影响很大,都对她另眼相待,誉她为“福星”。连县长也宴请这位35岁的英国女士,并请她坐在首位。席间,县长颇为好奇地询问艾伟德,说以她的能力,即使要宣教,为何不选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而要待在这穷乡僻壤,对骡夫和囚犯说故事。艾伟德沉静地回答说:“请从这窗口望出去,那许多身背重担,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苦力;再望过去那田野的农夫,茅屋内的女人;还有那些赤身露体、饥饿的孩子们。啊!这些穷苦、忧伤、饥饿的人们,绝不是上帝的意思,上帝要每一个中国人都充满希望和快乐。” 县长被她的话深深地打动了,以致于站起来当众郑重宣布:“儒家的教导存在我头脑里,但我看出基督活在艾伟德的心里。从今以后,我要作个基督徒。” 艾伟德马上恭喜他做出这关乎永生的决定。
有一天,艾伟德行走在大街上,忽然看见路旁有个妇人在卖一个骨瘦如柴,满身脓疮的小女孩。那妇女看见艾伟德,就请求她把孩子买下,否则这孩子必死无疑。艾伟德动了怜悯之心,搜遍全身,把仅有的九毛钱给了她。于是艾伟德把小女孩领回到八福客栈,并给她取名叫“九毛”(Nine Pence),学名叫“美恩”。在艾伟德的爱心照顾下,九毛恢复了健康,慢慢成为艾伟德的小助手。不久,九毛在门口看见一个可怜的8岁小男孩,艾伟德又收留了他,取名叫“少少”。此后她再收养了一个孤儿“宝宝”,和一个8岁的女孩“兰香”。
1936年,艾伟德归化为中国籍,正式取中文名为“艾伟德”,成为首位入籍中国的西方宣教士。从此后她不再是“洋鬼子”,她可以骄傲地说:“我是中国人”。1937年7月芦沟桥事变,中日战争爆发。不久,阳城也受到了日军的轰炸。有一次,一颗炸弹击中了八福客栈,艾伟德被压在瓦砾堆下, 一时失去了知觉。等她被救出时,发现只受了点轻伤,其他人则安全无恙。为避开战火,艾伟德带着她的孤儿们,和几个基督徒一起,疏散到地处山区的北柴庄。在一个窑洞里,她用仅有的一些急救药品救助伤员。直到日军离去后,她和难民们才返回阳城。
1939年2月,艾伟德得悉日军暂时撤离泽州,回大城市过冬去了。于是她专程前往泽州去看望内地会的同工们。此时,司米德夫人已经离世,戴维斯夫妇(David & Jean Davis)负责宣教站工作。他们是英国人,宣称保持中立,方才得以平安。但有一天夜裡,几个酒醉的留守日本兵,突然闯入宣教站,狂喊乱叫耍酒疯。艾伟德前去与他们交涉,被一个士兵用枪托击中,当场昏倒在地。醒来的时候,有戴维斯夫妇在旁照顾她,才无大碍。不久,有两位年长的宣教士要回国,须由戴维斯送他们到烟台等船。临行前,他们嘱咐艾伟德代为看守宣教站,并向她申明差会的严守中立之政策。
暂住泽州期间,艾伟德接受了美国《时代》(Time)杂志记者的访问。《时代》创办人鲁斯(Henry Luce)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路思义的儿子,他出生在中国,非常支持和同情中国的抗日战争。采访中,艾伟德回答说:“我代表的宣教团体是中立的,但我恨恶日军的暴行,也不能缄默不言。当然,我是中国人,也会把所知道的日军行踪,报告中国方面。……我虽然鼻子很高,但心是中国人的,不能无视日军的暴行。” 艾伟德的这番话通过《时代》杂志报道后,激怒了日本军方,遂下令清乡日军,并四处张贴告示“悬赏捉拿小妇人艾伟德”。
当时泽州的宣教士收留了200多名孤儿,这也是艾伟德主要的看守任务之一。1940年初,出于安全考虑,她派自己的助理晋本光,转移100多名孤儿到西安。现在,艾伟德知道自己和宣教站处于险境,经权衡利弊后,她决定带领剩下的100名孤儿逃往阳城。逃亡路上,遭到日军飞机的低空扫射,她只觉得肩头上好像被猛击一拳,就摔下马来,后来才发现是中了枪弹。到阳城后,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形势十分严峻。为了孩子们的安全,她和同工们商量后做出惊人的决定:由她亲自带领100个孩子,远走陝西扶风,因那里有他们的基地。因此才有了“千里大迁移”的壮举。
从阳城到西安大约有480公里的山路。临行前艾伟德去向县长告别。县长好心地提醒她,日军到处悬赏捉拿她,路上千万要小心。当艾伟德说到她要带100名孤儿一起去时,县长吓坏了,劝她千万别做傻事。但艾伟德坚持说,这100个孩子都是神赐给她的,一个也不能丢下。县长见无法阻止她,就关照说:“路上要有足够的口粮呵。我派几个人,扛上几袋小米,送你们一程;但只能到黄河为止,剩下的路就靠你独自支撑了,我只有为你祷告了。”
很快,这支特殊的队伍就踏上了征程。100个孩子中,最大的是16岁的女孩素兰,最小的只有4岁;其中还有艾伟德收养的四个孩子。队伍前后由成年人压阵,小孩子们互相搀扶着,最小的孩子,由几个成人用箩筐担着,而艾伟德则前后招呼着,还不停地抱着疲累的孩子赶路。为避开日军,她们不敢走大路,只能在当地人带领下在崇山峻岭间踽踽而行。小孩子们一路上吃喝拉撒穿用,都需要照顾,其艰难超过人的极限。
经过12天艰难跋涉后,他们到了黄河边上,但没有船无法渡过。他们在黄河边足足等了三天,粮食也快告罄。艾伟德焦急万分,只能不住地祷告。到第四天,终于盼到一只国军的船从对岸驶过来,靠着这只大木船,100多人分三批渡过了黄河,进入到国军的防区,总算脱离了险境。后来在军人们的帮助下,他们搭上了开往西安运货的火车,但中途因桥梁被炸毁,他们只好下车,余下的路要徒步走向西安。但这段路谈何容易!他们必须要徒步穿过以险峻着称的崤山。那段山径蜿蜒于高山绝谷之中。他们需要像古代士兵那样,攀山越岭往前行。他们以惊人的信心和勇气,攀行半个多月,面对重重山峦,体力已经到了极限。有一次他们瘫倒在地,再也走不动了。艾伟德心力交瘁,看着瘫软在地哭泣着的孩子们,她放声大哭起来,孩子们也跟着她哭,一时哭声震天。但哭过之后,还是要挣扎着往前走。当时只有一个信念:一定要走出去,一个也不能掉队。终于有一天,有大片密集的房屋出现在他们的面前,经对照地图艾伟德确认说:到潼关了,我们有救了!潼关是陝西的东大门,距西安大约135公里之遥,到达这里,意味着他们已经穿过崤山之险。在潼关,他们再次扒上了运煤的火车,中间又转乘几辆汽车,经历千辛万苦,总算抵达西安。
在宋美龄创办的一所孤儿院里,艾伟德把孩子们集合起来点名,结果发现100个孩子一个都不少时,她突然就昏过去了。待她醒来时,发现已躺在西安浸会的医院里,医生告诉她:你脑部受伤,患有肺炎,还得了伤寒,肩上还有一颗子弹,又发着高烧,加上营养不良,你的病情很重。而艾伟德却喃喃地呼唤:“我的孩子们在哪里?……我有一百个孩子。” 直到听说孩子们都好之后,才安下心来。在当时的条件下,她能够活下来堪称是一个神迹。她在医院里治疗了一年之后才出院,那时100个孩子都已经去了最终目的地——陝西扶风。
1942年初,艾伟德开始在郿县的难民营工作,那里距扶风和西安不远,她可以有机会经常去看望她的孩子们。不久,她又在西北各地从事宣教活动。1944年至1945年期间,她在甘肃兰州和四川成都服务穷人和麻疯病人,甚至传福音到喜马拉雅山麓。直到1948年,她的身体又累垮了,司陶卫医生(Dr. Olin Stockwell)劝她回英国休养并探望父母,然而离家已经17年的艾伟德此时竟一文不名,连路费都要靠医生为她筹措。1949年春,47岁的艾伟德终于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英国。虽然经过多年战乱,其父母和兄姐都还健在。在家中,她享受到久别重逢的天伦之乐,但她心里却时时牵挂着那多灾多难的中国,因为中国已经成了她的祖国。在此期间,她写下了自传《我的心在中国》;伦敦一位名叫莱德伍德(Hugh Redwood)的新闻记者采访她之后写了一篇专访;之后英国广播公司的作家艾伦•伯奇斯(Alan Burgess)又以她的事迹为底本,写作出版了传记小说《小妇人》(The Small Woman),不但成为畅销书,而且英国BBC广播电台还将之改编成广播剧,连续播出。这些使艾伟德成为英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1957年,更有美国二十世纪福克斯公司(20th Century Fox)与艾伟德签约,根据她在阳城的传奇故事改编成电影《六福客栈》(The Inn of the Sixth Happiness,注意:这里将“八福”改成了“六福”),由著名影星英格丽•褒曼主演,更使艾伟德扬名全世界。她的事迹感动了欧美无数青年人献身宣教,也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
但艾伟德并不喜欢这许多名誉,她只把自己看为一个普普通通的宣教士。她更不喜欢那部把“八福客栈”改为“六福客栈”,并且把她的经历改成面目全非的、英雄加美人的爱情电影。艾伟德一生中既没有花前月下的爱情经历,也没有和任何男人接过吻。为此她感到既气愤又羞愧,从来不去看这部电影。
1957年,艾伟德决定重回中国,但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拒绝入境,只好进入香港,在那里从事难民救助工作。后因其中国护照在香港的居留签证期限已到,她又转去海峡对岸的台湾。当她坐船离开香港时,遥望大陆,不禁泪流满面,久久难以抑制。
到台湾后,艾伟德延续其过去的慈幼工作。1959年,艾伟德与世界展望会合作,在台北木栅创办“艾伟德孤儿院”。同年,美国展望会邀请艾伟德到美国作旅行布道,美国听众这才惊奇地发现,她并不是电影中那位美丽的女星,而是一位矮小苍老的小妇人。不久,她又应邀到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地巡回布道与演讲。后来,她再次回英国时,英国BBC 再次为她制作出一个电视节目“This Is Your Life”。其后坎特伯雷大主教会见了她;伊丽莎白女王也邀请她到白金汉宫相叙。她自然不会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请求女王帮助在台湾的孤儿们。
1962年艾伟德另觅新址在北投创立了“艾伟德儿童之家”,同时她也积极参与欧美及台湾各地的奋兴布道工作。由于早年与宋美龄相识,艾伟德到台湾后,常常参加她所组织的妇女祈祷会,一同为中国祷告。她常以自己的经历鼓励青年人说:“不要耽心你所受的教育,上帝不要你呈验毕业文凭,只要你对蒙召的事,凡事忠心。” 她如是说,也如是行。
1969年12月,台湾岛笼罩在寒流侵袭之下,气温湿冷,使艾伟德感染A2型流行性感冒,并引起肺炎併发症。1970年元旦傍晚六点,好友史可梅女士(Kathleen Langton-Smith)请基督教诊所滕华宁医生(Dr. Heikki Tenhunen, 1932-1994)来为她诊治,但终因病情严重,于1月3日夜间在家中辞世,享年68岁。
她去世的时候,要求把自己埋葬在中国,但在当时的条件下,只能安葬于台湾。当时许多人都愿意捐献土地给她做墓地,最后由艾伟德的生前好友,基督书院(Christ’s College)院长贾嘉美牧师(Rev. James R. Graham Ⅲ,1898-1982),提供该校校园内的一块土地,作为艾伟德的墓园。该墓园位于基督书院内的礼拜堂西边,环境幽静,面对淡水河出海口,朝向中国大陆。贾嘉美牧师说:“艾伟德生前常来基督书院讲道,基督书院捐赠这处园地,是表示对艾伟德的敬爱。” 1970年1月24日下午二时,艾伟德追思礼拜在台北市立殡仪馆景行厅举办,蒋中正总统题颁挽联“弘道遗爱”(此四字亦复刻在墓碑上),蒋夫人亦赠一十字架花圈。参加追思礼拜的约有一千余人,将会场挤的水泄不通。下午三时半在书院礼堂举行安葬礼拜,由美国驻台海军军中牧师马立德(Rev. Lowell Malliett)作祝福祷告,随后盖棺安葬。遵艾伟德遗嘱,下葬时头部朝向中国大陆,以示她心对那片土地的眷恋。
资料来源
- Alan Burgess, The Small Woman. 1957.
- Gladys Aylward, The Little Woman. 1970.
- Phyllis Thompson, A London Sparrow. 1972.
- 张继新、虞佳一、余玲玲编译,《八福客栈》,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6年。
- 魏玉琴摘译,《把此山给我》。校园出版社,1979年。
- 纪录片,Gladys Aylward, the Small Woman with a Great God,2008年。
关于作者
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