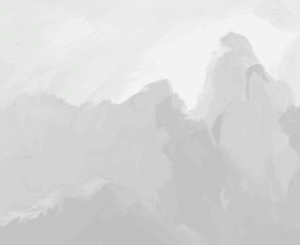一、早年生活
伯駕(Peter Parker)於1804年出生於美國麻薩諸塞州弗蘭明罕(Framingham)一個具有濃厚清教徒傳統的農家,是家中唯一的男孩,有兩個姐姐和一個妹妹。他們在父母的言傳身教下,過著敬虔、純樸的生活。因家境比較貧困,伯駕年少時除上學外,課余時間還要到農場勞作。每禮拜日和父母家人一起到教會做禮拜,在信仰上受到很好的熏陶。1820年4月15日,16歲的伯駕受洗成為基督徒,當時他就立將來成為一個宣教士,有朝一日到異邦去傳福音。中學時期,他父親去世。1827年,伯駕考入阿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靠打工賺錢支持自己讀書。三年後,他考入耶魯大學 (Ya1e College)。由於耶魯承認他在阿默斯特學院的全部學分,所以他直接升入四年級學習。在耶魯他修讀了解剖學、化學、植物學、地質學、天文學和哲學等課程,於1831年9月畢業,獲得學士學位。在耶魯期間,他不但精於學業,而且努力追求過一種聖潔的基督徒生活。在其日記中,經常出現的一句話就是:“我願更加聖潔、更像耶穌。” 1831年4月間,當“美部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美國最早的海外宣教團體)宣教士安路福(Rufus Anderson)來耶魯校園主領福音聚會時,促成了伯駕獻身做一個宣教士的決定。於是他向美部會提出了申請,受到接納後,重回耶魯接受神學和醫學的訓練。1834年3月,伯駕獲得醫學博士學位並醫生資格;5月被美國長老會按立為牧師;6月1日又在紐約長老會教堂正式任命為宣教士,三天後即接受美部會的派遣去中國廣州,從而成為美國第一位來華醫療宣教士。
二、行醫宣教生涯
1834年6月4日,伯駕告別親友,從紐約搭乘“馬禮遜號”輪船啟程,繞道好望角前往中國,於10月26日到達廣州。一個多月後,伯駕轉往新加坡,在那裏學習中文,從事醫療宣教十個月後,再次於1835年9月來到廣州。同年11月1日,伯駕決定在廣州開設醫局。在英美商人捐助下,又得到廣州十三行總商伍秉鑒的幫助——出租新豆欄街豐泰行房產的一部分給伯駕開設眼科醫局,年租金500元。該醫局當時稱“新豆欄醫局”,於11月4日開始接診病患者。不久因擴大業務而更名為“仁濟醫院”(Hospital of Universal Love,今中山醫科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的前身),意即“本耶穌基督大愛,以濟世為懷作宗旨”,伯駕自任院長。雖然此前曾有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郭雷樞(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等人在澳門辦過醫療診所,但規模都很小,並且沒有延續下來。所以伯駕所創辦的這所醫院被認為是中國境內第一所正規的、現代化的西醫院。
新豆欄醫局一開始就頗具規模,有可容百多人的候診室,兼備40余張病床,新式儀器一應俱全。伯駕的專長本是眼科,因此當初只打算為眼疾患者免費服務,贈醫施藥。其時因清政府的閉關政策,使中國百姓對西醫心存疑惑,不敢前來就醫,所以醫局開業的第一天,雖然標明免費治療,整天竟無人問津。次日一位飽受眼病折磨多年,卻又無錢求醫的婦女,抱著姑且一試的心情,戰兢前來就診,從此揭開了西醫在中國治病的序幕。此後由於伯駕高明的醫術,和藹可親的服務,很快就贏得廣州百姓的信任。隨著伯駕治愈病人的數目增多,醫局的名聲愈加增大,前來求診的病人也就大增。根據紀錄,醫局開診後僅17天,前來求診的人數就達到240位,內中還包括好幾位衙門官員。為了使日漸增多的病人能夠循序就醫、提高效率,伯駕在病人進門後,先發給竹片制成的長方形號牌,然後病人就按照號牌上的號碼,循序進入診療室接受治療。據說這種已為今日世界各醫院普遍采用的“掛號制度”,就是源自於伯駕在新豆欄醫局的這套設計。新豆欄醫局開設之後第一年,一共診治病人2152人次,到醫院來訪問、參觀者不下六、七千人次。
在醫院日常診療工作中,大部分病人均由伯駕親自診治,診治病人數最高曾達一天200多人次。對就診病人,伯駕均嚴格實行病歷登記制度,除病人的姓名、性別、年齡、籍貫外,對處方用藥、治療效果、手術時間長短以及取出的腫瘤或結石的大小、重量等,都有詳細紀錄。在他的病歷記錄中,有一位13歲的小女孩,面部長有巨型腫瘤,從頭部太陽穴一直向下生長到右邊面頰,整個右眼幾乎都被遮閉掉。伯駕在征得家長同意後,經過周密的準備,為這女孩進行了切割手術。當時還沒有麻醉劑,只是在手術前讓患者服用了一些鴉片劑,然後將女孩眼睛蒙住,把手腳捆綁在手術臺上實施切割。最後伯駕成功地割下這顆一磅多重的腫瘤,這是伯駕來華後所施行的第一例外科手術。此後每次實施割治手術前後,伯駕都特別請畫家詳細繪下病人的病狀,保存下來,歸入檔案,以供日後教學及研究參考。當時十三行有一位華人職業畫家,名叫關喬昌,西人稱他為琳呱(Lam Qua),有感於伯駕免費為華人治病,自願免費為伯駕畫下各種病狀,成為生動的病歷資料保留下來。如今尚存有110幅,其中86幅在耶魯大學醫學院圖書館(Yale Medical Library),23幅在倫敦蓋氏醫院的戈登博物館(Gordon Museum at Guy’s Hospital),一幅在波士頓的康特威圖書館(Countway Library);其中有30多幅是腫瘤患者的畫像。凡看過那些奇形怪狀、醜陋猙獰的腫瘤病狀的人,無不敬佩伯駕的醫術與愛心。伯駕在中國近代醫學史上首創多項紀錄,如割除扁桃腺(1836年)、割除膀胱結石(1844年)、使用乙醚麻醉(1847年)、采用氯仿麻醉方法(1848年)等。
伯駕每天清早起床,簡單就餐後,就為前來求診的人看病治療,往往一直忙到深夜。辛苦勞累不說,生活作息全無規律。但當他看到一個個病人經他治愈後離去,就心裏快慰,感到再苦再累都值了。他的服務體現了耶穌基督的博愛,中國百姓無論貧富貴賤,在他眼中皆一視同仁,他以行動見證了基督的福音。伯駕一直視醫療為傳揚福音的途徑。每次為病人施行手術前,他都迫切地為病人禱告,幫助病人信靠神,將他們交在最大的醫生耶穌手中,然後才進行手術。當痊愈後再同病人一起禱告感謝神,藉此使患者不但得到身體康復,更經歷到心靈的更新。
1840年鴉片戰爭爆發,仁濟醫院被迫停業。戰爭期間(1840-42年),伯駕周遊美國、歐陸、英格蘭及蘇格蘭等地,推動醫療宣教,招募醫療宣教士及募集宣教經費,同時也引進最新的醫學技術。1841年3月,37歲的伯駕與美國國務卿丹尼爾•韋伯斯特(Daniel Webster)的侄女哈烈特•韋伯斯特(Harriet Webster)小姐結婚。1842年11月,伯駕帶著他的新婚夫人返粵服務,此舉使其夫人成為第一位居留廣州的美國婦女。仁濟醫院復業時,已不限於眼科,改為一所綜合性醫院。伯駕在初設眼科醫局時,主要是治療眼病,後來應病人的需求,才增加診治其他病癥的科目,仁濟醫院故而成為一間內外全科的醫院。
伯駕在華行醫十幾年中,先後診治過病人約53,000余眾,內中上至兩廣總督耆英,下到渾身長滿疥瘡的乞丐,他都無分貴賤,一視同仁,秉承耶穌基督的大愛,一律細心救治。在他所挽救的許多生命中包括第一位華人牧師梁發在內,伯駕曾說:“我一生之中即使未做過其它善工,只恢復了這個為上帝所愛的仆人的健康,我也就不枉為人一世了。”(《梁發傳》,輔僑出版社,第88頁)。後來梁發常到仁濟醫院來,向病人傳福音,也為伯駕分擔勞苦。
1838年2月21日,第一位來華美國宣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郭雷樞和伯駕,以及商界人士在廣州聯合發起成立了“中國醫藥傳道會”(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郭雷樞被推為主席,伯駕為副會長。不久郭雷樞回英國長住,伯駕就成為實際的負責人。該醫藥會在聯系早期醫療宣教士方面發揮了很大的功能。1839 年時,在華宣教士中只有兩位醫療宣教士;因著伯駕的推動,到了 1842年有更多的醫療宣教士陸續來華;五十年後,已經有61家醫院、44家藥房、100多位醫生和26位女醫生在華從事醫療宣教,許多華人也因著他們的愛心醫療而接受基督教信仰。
伯駕的醫院除了救治多人的生命外,還拯救了不少失喪的靈魂。由於仁濟醫院實行免費治療,且療效顯著,不久便聲名遠播,不少外地患者也前來求診,醫院門庭若市。為了解決人手不足問題,伯駕於1837年招收了3名華人青年,以半工半讀和帶徒弟的形式 ,向他們傳授西方醫術。其中最有成就者當屬關韜,他是那位經常為伯駕繪制病歷的畫師關喬昌的侄子。關韜約於1838年跟隨伯駕學醫,由於天性聰穎,且好學不倦,數年後即能獨立施行常見的眼疾手術,以及拔牙、治療脫臼、骨折等工作。因其品學兼優,深受伯駕之器重。每逢休假,伯駕就委任關韜代為主持診療工作。他精湛的醫術,良好的醫德,深受中外人士贊譽,亦首開中國人師從西人學習西醫之先河,畢業後成為中國土生土長的第一位西醫醫師。
三、伯駕與鴉片戰爭
伯駕是在中英鴉片戰爭的前夜來到中國的。當時清政府實行閉關自守之政策,國家經濟制度是個龐大的自給自足經濟體系,西方剩余資本和剩余產品難以進入中國。另一方面,由於西方各國對中國茶葉、生絲需求龐大,反而使中國成為對外貿易的出超國。這使那些急於打開中國市場的西方國家,沮喪之余,想方設法打破這一困局,以滿足其在數百年間飛躍發展起來的經濟擴張需要。鴉片貿易因此成為突破中國政治經濟防線的力量,於是鴉片急劇流入中國,大大損害了中國人的體質和精神,也給清政府帶來巨大經濟和政治危機。
1839年初,清廷派林則徐為欽差大臣南來廣州,查禁鴉片。英國鴉片商敷衍他,不甘盡數交出鴉片。於是林則徐在3月24日派兵包圍了“夷館”,當時被困的外國人有三百多名,伯駕也在其中。經過一番對抗,三天之後“夷館”的領事義律屈服,遂命英商陸續繳清鴉片,不久英僑全部撤至香港和澳門。由於林則徐強硬的禁煙之舉,造成清朝政府與西方列國之間關系的緊張。1840年春,英國決定對中國出兵,6月,英國軍艦抵達廣東沿海,鴉片戰爭爆發。
當英僑撤至香港和澳門之際,伯駕卻獨自留在廣州,醫院照樣開診。到1840年6月之前,來醫院求醫者仍近一萬人次。因為他醫術高明,使其在廣東從民間到官方都頗有名望,與中國官員多有聯系,連林則徐也先是請他開藥方為鴉片煙客戒毒,繼而請他為自己治療疝氣。林則徐本來就有疝氣病,來廣州後因勞累過度,舊病復發。7月,林則徐派人與伯駕取得聯系,向他討教兩件事:其一,西方有無戒除鴉片的特效藥;其二,能否治療疝氣病。前者為公,後者為私。伯駕回復,沒有戒除鴉片煙癮的特效藥,但治療疝氣病有辦法,不過要病人親自來,因為他要給病人量身定制一個疝氣帶。林則徐身為欽差大臣,覺得不好把自己身體的隱私部位給外國人看,這是有失“官體”的事,於是就找了個身材和自己相仿的人做替身,派他去見伯駕。伯駕雖然對林則徐的做法難以理解,但還是給林則徐建了一個病歷,上記著:“病案6565號,疝氣,林則徐欽差大臣。” 並為其診斷了病情,托人帶去了藥物和疝氣帶。經過伯駕的治療,林則徐的病情明顯好轉。
伯駕隨後為林則徐提供了治療鴉片危害的詳實資料,還曾為林搜集提供海外資料,幫助翻譯書報。《萬國律例》(Law of Nations)的片段中譯,就是伯駕所作。這些資料,對於林則徐等開明官員睜眼看世界,研究西方文明,進行外交與戰爭決策起了一定的作用。此外,伯駕還曾通過林則徐派來見他的使者,贈送林則徐一份地圖、一本地理書和一個地球儀。
1839年7月,伯駕給林則徐寫了一封信,信中詳細闡述了他對中英局勢的看法。伯駕無疑是一位反對讓鴉片荼毒生靈的人,對林則徐的禁煙立場,及中國人民所受鴉片荼毒之苦,深表理解與同情。他稱自己“特別是中國的朋友”,表示對“鴉片煙魔”的憎惡;稱贊林則徐“廉潔、愛國和仁慈”。但他婉勸林則徐放棄對抗英國的激烈行動,試圖緩和一觸即發的中英緊張關系。同時他也不諱指出林則徐由於不了解西方法律和國際慣例的欠缺而可能導致的嚴重後果,並表示願意出面調解中英兩國的矛盾。最後他希望通過“體面條約”的形式,規範中外關系,達到使中國對外開放的目的。這大概是第一次有人向中國官方提出放棄閉關自守國策,實行對外開放,與世界各國建立新型國家關系的建議。無論伯駕當時的主觀動機如何,這一建議具有深遠的意義。盡管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林則徐及清政府沒能接受伯駕的建議,但對於以後中國政治的演變還是有影響的。伯駕這封信,與他主動與林則徐聯系的行動,顯示了伯駕希望通過影響中國統治階級上層人物,以圖建立新型的中西方關系,改變中國基本國策的願望。有史料證明,林則徐當年收到了伯駕的信,可是他沒有答復。也許是林則徐考慮到中西嚴峻復雜的情勢,不宜雙方見面。兩個月後,鴉片戰爭爆發,伯駕不得不關閉他的仁濟醫院,離開廣州前往澳門。三個月後,林則徐亦被革職。到1842年,鴉片戰爭最終以清政府戰敗,簽訂《南京條約》,割地賠款而宣告結束。
四 、政治與外交生涯
伯駕的仁濟醫院在鴉片戰爭中被民眾燒毀。戰爭結束後,伯駕一面復辦醫院,一面積極從事外交政治活動。隨著他卷入政治與外交活動日深,與中華民族對立也日漸加深。1844年,中美在澳門望廈村從事《望廈條約》談判時,伯駕應聘擔任美國公使顧盛(Caleb Cushing)的部分時間秘書兼中文翻譯。《望廈條約》又稱《中美五口通商章程》,中方談判對手是兩廣總督耆英,他曾經接受過伯駕的診治。由於伯駕精通中文,熟悉中國情況,又通過行醫與中國官員結交,這給他的談判工作帶來許多便利。原來在第一次鴉片戰爭後簽訂的《南京條約》中,對傳教問題沒有作出任何規定。這次經伯駕等人的力爭,在《望廈條約》中,加進了在華傳教自由之條款,對清政府采取弛禁基督教政策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特別是他與十三行巨商潘仕成等中方顧問的密切交往,促成了傳教條款的訂立和條約的簽訂。
由於伯駕越來越多地涉入美國的政治和外交事務,造成他與美部會之間的關系緊張,1845年終於被迫辭職,美部會也終止他作為該差會宣教士的資格,理由是伯駕把太多的時間用於醫療工作及外交事務,而忽略了宣教工作。同年,伯駕接受美國泰勒(John Tyler)總統的聘任,成為美國駐華外交代辦。1855年,美國政府正式委任他為駐華全權公使,仁濟醫院從此移交給美國北長老會宣教士嘉約翰(John Kerr)醫生,1859年遷入新址,改名為“博濟醫院”(Canton Hospital, Pok Tsai)。伯駕擔任駐華公使後,主張強勢外交,建議美國佔領臺灣,以保持“勢力均衡”,並與英法各國聯合提出修約要求,為美國爭取更大的利益。
五、晚年生活
1857年4月22日,駐華公使一職被列衛廉(William B. Reed)所取代,伯駕遂結束了他在中國的宣教和外交生涯,於1857年底偕妻回到華盛頓特區定居,從此脫離了美國政界,也再沒有來中國。兩年後,夫婦倆竟喜得一個兒子,是時伯駕已經55歲。另一令人稱奇的是這位在眼科、外科與麻醉等方面都可以列入世界一流的醫生,回國後竟然沒有再為任何人看病,好象他根本未曾當過醫生一樣。不過他對中國的關注卻未中斷,繼續與其在中國的友人保持聯系。當他得知博濟醫院在嘉約翰的領導下,在醫療宣教方面不斷取得進展時,心裏感到無比的快慰。當1885年博濟醫院為紀念伯駕開設醫療事業50周年時,他還寫信表示祝賀。
1859年,伯駕與美部會修好,並成為該差會的理事。1876年,伯駕在美擔任“中國醫藥傳道會”會長,同時受聘擔任美國國立博物館(Smithsonian Institution)的參議,以及耶魯大學校友會會長;他亦熱心於新成立的福音派聯盟。晚年期間他還撰寫了數本醫療宣教的書籍。伯駕前半生在中國的悲劇性經歷,是中國近代史上中西方文化、政治與軍事在激烈沖突中交匯的縮影;伯駕在美國度過他余下後半生,於1888年在其寓所中去世,享年84歲。
資料來源
- Gulik, Edward V. 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伯駕與中國開放》),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魏外揚著,《中國教會的使徒行傳》,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6年。
- Bowers, John Z., M.D., 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 (《西方醫學中國的殿堂》), USA: Tiosak Macy, Tr. Foundation, 1972.
- 金曾澄著,《中山紀念博濟醫院概況》,1934年3月。
- “中國首家西醫院今年170歲”,原載廣州日報,2005年3月30日,《南方網》: www.southcn.com/news
- “中國近代第一位西醫生——關韜”,《醫學集郵研究會》: yixuejy.nease.net/mhistor
- “西醫東漸與中國近代醫療衛生制度的肇始”,《智識學術網》 : www.zisi.net/htm
關於作者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