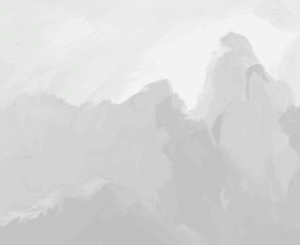巴富羲于1903年8月9日生于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市一个企业家的家庭。其父母敬虔爱主,共生了8个儿女,他排行第六,上有三个哥哥,两个姐姐,下有一弟一妹。在父母的熏陶下,巴家儿女们从小就去教会参加主日学和各种聚会,认识救恩,并受洗归主。巴富羲12岁时,当被问及长大后要做什么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做宣教士。”
父亲在事业上很成功,且非常热心于海外宣教。他希望儿女中能有五位成为宣教士,并乐意支持他们费用,不用宣教差会支持。巴富羲的长姊巴若兰姑娘(Miss Elizabeth Fischbacher)首先加入中华内地会,作为内地会宣教士工作了13年之久。她在山西时,曾与中国名牧杨绍唐牧师在洪洞神学院同工,一起培训中国传道人。后来她从内地会退休成为自由宣教士,到中国各处主领培灵奋兴会,在信仰上对倪柝声产生过影响,并曾在文字、翻译事工上与倪柝声同工。著名的圣光学校尹任先校长亦得到过她的帮助。巴富羲的弟弟巴辅胜教士(Theodore Fischbacher)在他以身殉职后亦加入内地会,并在中国娶妻生子,工作了15年,直到1949年才不得不离开中国。
巴富羲中学毕业后,考入医学院读书。先后取得爱丁堡和格拉斯哥大学的L. R. C. P和L. R. C. S.资格后,在不同医院里工作。接着自己在曼彻斯特开业,行医济世,前程似锦。
1931年5月,巴富羲从英文版《亿万华民》(China’s Millions)上读到一篇短文,是由一位在宣教工场上的宣教士“致青年人”的一封公开信。其中一段话深深打动了他:
“我们呼吁需要200位宣教士,经过了近两年尚未达此目标。你对这呼吁有何反应?或许你因不同的见解而反对,可是有没有想过,你若反对,当主再来的那一天,你将怎样响应他呢?”
巴富羲原本是打算到非洲宣教的。但读过这封信后,他心中有声音催促他立即写信给《亿万华民》的编辑,把自己受感要去中国宣教的心愿告诉他们。稍后,他写下这样的见证:“我反复思量:我学医到底是为了传福音,还是为了做医生?当看到今年六月份的《亿万华民》呼吁宣教士投身到中国去时,这呼召一直萦绕我心,挥之不去。” 就这样,他加入到内地会的宣教行列,成为200名宣教士之一。
1931年12月31日,巴富羲乘船离英前往中国,到达上海时已是1932年2月1日。当时上海刚刚发生了“一·二八事变”,因战事他们这批人滞留上海,不能及时赶赴安徽安庆语言学校参加语言训练。滞留期间,巴富羲参与救治国军伤兵。
几经耽搁,他们总算乘上满载难民的船,沿长江逆流而上,抵达安庆。随即投入紧张的语言训练中去。他们这期学习语言者,有来自欧美国家共72人。两个月语言训练课程结束后,巴医生和英国的赵立德教士(Raymond H. Joyce)、何仁志教士(George F. Holmes)、朱佩儒教士(William J. Drew)、美国的石爱乐教士(Otto F. Schoerner)和澳洲的柏爱生教士(Aubrey F. Parsons),共六位,一起被分派的新疆的迪化(今乌鲁木齐市)。
在内地会,巴富羲与其它宣教士一样,凭信心生活,婉拒父亲要在经济上对他的支持。他写信给父亲说:“……如今我已加入信心差会,一切皆祷告仰望主的供应。希望你能明白我不接受你的好意,不是受别人的影响,乃是基于我与神之间的关系。”
在上海滞留等待赴新疆时,姐姐巴若兰从山西洪洞赶来与弟弟相聚。分别多年,两人有美好的交通与分享。言谈中,姐姐明显感到弟弟灵性上的长进。
由于赴疆路途遥远,且战祸连连,各路交通受阻,最后巴富羲等宣教士决定自己开车赴新疆。先由新疆资深宣教士胡进洁牧师(Rev. George W. Hunter)到北京,与巴富羲从天津购买两辆福特货运车。然后,众人到北京集合,各人做了分工,购足配件与给养。经过充分的准备,终于在1932年9月13日正式启程。他们从河北省张家口市出发,穿过长城进入内蒙古。1800英里的行程,道路崎岖难行,有些地方根本没有路。途中还不时遭遇风沙、雷雨的袭击,但他们义无反顾,穿山越岭,跨过江河,穿过茫茫戈壁。一路虽经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但同时也经历了神奇妙的带领和眷顾。直到10月14日他们才进入新疆境界;10月17日到达哈密。就在目的地在望之际,他们又赶上新疆回族首领马仲英之叛乱。在道路不通,燃油缺乏的情况下,他们又几经周折、迂回,直到11月9日才到达迪化。
这六位新宣教士被交由在当地工作了23年之久的马尔昌(Percy C.Mather)教士照管。由于战乱,迪化物价飞涨,物品奇缺。多亏马尔昌冒险到城外农村去购买粮食、蔬菜和肉类,才使他们免于挨饿。战争使伤亡人员剧增,这时,有乡绅父老出面,联同政、商、学和宗教界人士组成红十字会和慈善会,救助伤兵。在胡进洁牧师的带领下,所有宣教士都投入到治病救人的行列中去。他们照顾120多个伤病员,每天从早到晚,非常辛苦。但他们也借此接触到劳苦人民大众,把福音传给他们。
巴富羲医生终日在简陋的医院手术室里,为人做手术、疗伤,工作量极大,体力大大透支。从1933年4月17日他写给同做医生的妹妹的信中,可见一斑:“这是一场混乱的战局,但是主奇妙地保守我们经过。虽然在枪林弹雨中,我们一点也不害怕。……在前省长的要求下,我答允做急救和动大手术 ……,因为大多是刀伤和枪伤,但伤兵源源不绝……。我首次进入医院时就见到一个股骨五处裂开的伤兵,实在恐怖!试想想300多名大小伤势的兵,有许多人尚未获救护,整个医院实在骯脏、气味难闻……。我自己则忙不过来,没有仪器,甚至没有药物,也许要学习神迹医治吧。”
5月6日他写给亲人的信,是他的最后一封家书,从其描述中,我们可以得知他在世最后一段日子的真实处境:“我真的没有半点自己的时间,因而不常执笔。一天晚上因为有紧急状况,一位白俄领袖,一位军官和两个士兵与我一同骑马赶去,匆忙中我忘记拿件厚外套。不过那匹马像野马般地风驰电掣,使我出了一身大汗。回来时因为戒严令,我们在城门外等了半个多小时。这里日间炎热,但入夜则冷起来,再加上入城后每个岗位都要叫口令才得通过。回到家中后,感到有点着凉。加上忙个不停,睡眠不足。在三间医院中共有400多位伤兵。在我的特别医院里就有125个重伤者。…… 这些伤兵许多人二、三个月没洗过澡,污秽不堪。他们没有足够的营养食物,抢救的人手少,以致全部工作都落在我们这些工作过度的外国人身上。…… 这三个月让我走进了中国人最真实的生活中,不然也许要过许多年才有这样的机会。”
由于巴富羲医生每日接触许多伤兵,加之身心处于过度劳累之际,结果不幸染上了致命的伤寒。5月11日,正当他在医院中忙碌时,突感心胸绞痛,疑为心脏病,便回家休养治疗,随后却发起高烧来。这样时好时坏地过了两周,正当渐有起色之际,5月26日夜晚病情却突然转坏。到27日清晨,这位爱人如己的医疗宣教士竟不治而逝。从巴医生1932年2月1日抵达上海,同年11月9日到达新疆乌鲁木齐宣教,到1933年5月27日因染伤寒而离世,他在中国总共才度过了一年三个月又26天,而在新疆仅工作了六个月又18天,去世时还不满30岁。
巴富羲医生因救死扶伤不幸染病而逝的消息传到英国伦敦办事处后,引起很大震撼。《亿万华民》的主编海恩波先生(Marshall Broomhall)在是年底前发行了纪念巴医生的传记,书名是《为何枉费?》(To What Purpose?)。
巴富羲的同工柏爱生教士在其6月所写的报告里,如此记道:“巴医生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毫无保留地去抢救那些受伤的人。他对工作的认真,不仅让我们深深地受到激励,并且城里每一个人都对他心怀感激。政府大小官员都公认他真是个义薄云天,舍身取义的人。政府在追悼他的挽联上面写着‘舍己救人’四个大字。”
资料来源
- China’s Millions, China Inland Mission, North American Edition. 中华内地会月刊北美版《亿万华民》1931年第173页;1932年第125、158、188页;1933年第13、28、38至39、101-102、127、137、175、188页。
- China’s Millions, 英国版(London Edition)1931年第219、225、239页;1932年第14、114、122、155、202、217页;1933年第27-28、58、136、144页。
- Broomhall, Marshall, To What Purpose? China Inland Mission, 1934.
- The Register of CIM Missionaries and Associates 《内地会宣教士及伙伴宣教士名录》。
-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1916.
- CIM List of Missionaries and Their Stations, 1910, 1931.
- Directory of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24, 1927.
关于作者
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