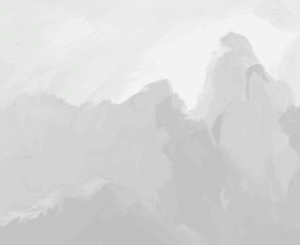十九世纪来华的英国圣公会宣教士、翻译家、报人、教育家和慈善家;近代西学东渐的巨擘,有“西学传播大师”之誉。在华35年中,有28年在江南制造局从事译书工作,翻译了大量的自然与社会科学着作;他还创刊了科学期刊《格致汇编》,并参与创办了“格致书院”,为向中国引进、传播和普及近代科学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此清政府授予他“进士”和三品官衔,颁赐他“三等一级双龙宝星。”他还在中国创办了盲童学校和盲女学校。
一、早年生活
傅兰雅(John Fryer)是苏格兰牧师之子,于1839年8月6日出生在英格兰肯特郡海德镇(Hythe, County of Kent)。受父亲的影响,自少年时代起就十分向往中国,梦想有一天能去中国宣教。父亲虽然只是一个小镇教会的牧师,却十分关注东方,特别是中国的宣教事业。傅兰雅年少时,经常跟着父亲去听那些从中国回来的宣教士举行的报告会。在日后的自传中,他回忆道:“在我的孩提时代,没有什么东西能比阅读我千方百计搞到的有关中国的书,更令我愉快。我太想去中国了,因此同学们给我取了一个绰号叫‘中国迷’(Sinophile)。”傅兰雅高中毕业后,曾在布理斯托(Bristol)的一所小学任教,遂爱上了教育,不久入读伦敦海伯雷师范学院(Highbury Government Training College),靠政府奖学金修完全部课程,于1860年毕业。
二、在华初年兴教与办报生涯
1861年初,傅兰雅接受英国圣公会派遣来华担任香港圣保罗书院(St. Paul’s College)校长,时年22岁。圣保罗书院的学生多数来自香港、澳门和广东的贫苦家庭,故大都能刻苦读书,毕业后就职于洋行、航运和教育等部门。中国近代著名外交家伍廷芳即为该校毕业生。傅兰雅很快显示出自己的语言天赋,在仅仅两年时间里,他不仅掌握了汉语,而且还学会了广东方言。为了进一步学好官话,1863年,傅兰雅前往北京,与包尔腾(John Shaw Burdon)、丁韪良(William A. P. Martin)等人一起,在北京同文馆担任英文教习,同时学习北京官话和中国经典史籍。1865年,傅兰雅又返回上海,出任英华书院(Anglo-Chinese School)院长。该书院原名“英华学塾”,是由上海外国侨民发起筹办的一所高档学校,其办学原则大致有四:第一、致力于招收富家子弟入学,提高收费,以确保学校资金雄厚;第二、採用英语教学;第三、聘用本地饱学之中国老师,教授中国传统的经史学科;第四、学校必须授以宗教教育。英华书院的学生多来自于上海、广东、厦门、宁波等地商贾和买办的子弟,其后出了不少名人,如清末政论家和思想家郑观应便是傅兰雅的学生。
除办学外,傅兰雅还担任英商字林洋行的中文报纸《上海新报》的主编,这是西洋人在上海创办的一份中文报纸。傅兰雅任职后,不仅要扩大报纸的发行量,还要使它成为启蒙中国的工具。他不仅要中国的知识分子能够读到这份报纸,还要将其影响扩大到官府乃至朝廷里去。通过办学与办报,傅兰雅为自己未来踏入中国的上层社会积累了资本,铺平了道路。
三、江南製造局译述生涯
1868年,晚清重臣曾国藩在上海创建了江南制造局,不久在局里开设了一个翻译馆,因为他认为“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中国许多科学家如徐寿、王德均、华蘅芳、李善兰和徐建寅等人,都进入该馆译书,并高薪聘请傅兰雅等西学人士,共主翻译之事。傅兰雅高兴地接受了聘用:“我现在开始做我想做之事了。我从来就喜欢科学,但一直未找到时间和机会研究它。我应该说,充任中国政府的科技着作翻译官,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职业。它受人尊敬,无比光荣,而且有用。这是我的人生新纪元。”实际上,这也是中国近代科学启蒙史的新纪元。傅兰雅遂辞去英华书院之职,受聘为翻译馆译员,专门从事西方科技书籍的翻译工作。他起初或许没有想到,他要在江南制造局度过长达28年的译书生涯,并由此成为开中国近代科技事业之先河的人物。
傅兰雅一进入翻译馆,即与徐寿等中国学者合作,开始着手制定详细的翻译计划,定购各种图书备翻译用。傅兰雅从一开始就是最主要的口译者,经他口译的科技著作数量最多。从 1869 年起,先后在翻译馆供职的口译人员还有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金楷理(C.T.Kreyer)、林乐知(Y.J.Allen)等人。在洋务运动时期,江南制造局是当时最大的翻译科技著作的机构,该局译书大致代表了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所能了解的西方科技知识的最高水平。而傅兰雅口译各书,又是该局译著的代表作。经他口译的译着多达113 种,其中包括数学、物理、化学与化工、矿冶、机械工程、医学、农学、测绘地图、军事兵工等书种。在这些译著中,有的是对有关学科的首次系统介绍,有的则为已翻译介绍过的学科提供了更新、更好的译本。比如,《决疑数学》是介绍概率论的第一个中译本;《代数术》和《微积溯源》是比李善兰和伟烈亚力的有关译著内容更为丰富、译笔更为流畅的译作;J.廷德尔(J. Tyndall)的《声学》(1869)和 H.诺德(H. Noad)的《电学》(1867)是最早、最全面系统介绍声学和电学知识的译著。在19世纪晚期西学译介的领域中,傅兰雅具有相当高的声望。他在数学领域的译介尤为突出,所译出的《运规约指》、《代数术》、《微积溯源》、《算式集要》、《三角数理》、《数学理》、《代数难题解法》等数学著作,涉及近代数学的几何、代数、三角、微积分等多个分支。这其中绝大部分是他和著名数学家华蘅芳合作译成,在当时中国数学界具有很高的评价。傅兰雅还与徐寿翻译了多种化学著作,其中 D.A.韦尔斯(D. A. Wells)的《化学鉴原》(Principle of Chemistry,1858)是最早的无机化学译著之一;《化学鉴原续编》(译自 C.L.布洛克萨姆(C. L. Bloxam)着 Chemistry(1867)的有机部分)是第一本有机化学中译本;而《化学考质》和《化学求数》则是根据德国分析化学大师弗雷森纽斯(Fresenius)关于定性分析、定量分析的经典名著译出,内容十分丰富精深;再加上介绍物理化学知识的《物体遇热改易记》,当时译出的化学书籍已经较成系统,初具规模。傅兰雅与他人翻译的各种技术著作,除兵工外,在当时多属绝无仅有。关于采煤、勘矿、开矿、冶金、铸造、机械原理、机械制图、蒸汽机技术、酸碱制造、电镀、照相等众多领域,都有专门译著,其中以《西艺知新》丛书正续集、《宝藏兴焉》、《化学工艺》和《造船全书》等最为重要。医药学译著以《西药大成》和《法律医学》最巨,后者是第一部法医学译著。
傅兰雅以宣教士布道一样的热忱和献身精神,向中国人介绍、宣传科技知识,以至被人称为“传科学之教的教士”。在当时西方近代科技知识输入中国的历史进程中,没有任何外国人比他做得更多,甚至也很少有中国人比他做得更多。在其翻译生涯中,傅兰雅单独翻译或与人合译西方书籍计有150部,合1000卷,是在华外国人中翻译西方书籍最多的人,其内容以科学、工程和军事方面为主外,旁及地理、历史、政治、外交、社会等各个领域。从这批科技译著的价值看,远比明末清初时期欧洲耶稣会宣教士所介绍的西洋技艺高超得多。傅兰雅所译介的书籍是西方工业革命的成果,已是机器时代,而且都属19世纪欧美所出版的最新科技著作。在影响方面,也远比耶稣会士所做的更为广泛,耶稣会士仅在宫廷内部向少数愿意学习的官僚和学者介绍西学,接触面非常狭窄;而傅兰雅等人的译著却是在第一代科技人员和工人中传播,同时那些参与翻译的中国学者的科技知识也随之提高,掌握了18、19世纪最新的声、光、化、电和军工、冶金、采矿等知识和发展趋向。这些成就对晚清知识分子吸收西方科学知识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四、创办“格致书院”与《格致汇编》
在艰苦而寂寞的译书工作之余,傅兰雅还以其个人的力量,积极传播科技知识。1874年,傅兰雅与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Walter H. Medhurst)商议后,由麦华陀出面倡议建立“格致书院”,作为研习和传播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知识的场所。倡议一出,得到了各方热烈响应。同年3月24日,由傅兰雅主持召开了筹备会议,提出筹办格致书院的目标、宗旨和计划,产生出由傅兰雅、麦华陀、美国植物学家福勃士(Francis B. Forbes)、英国汉学家伟烈亚力,和清朝官办招商局总办唐廷枢五人组成的筹办委员会,后又增加徐寿和徐建寅父子共七人,筹措办校事宜。1876年6月22日,格致书院正式开班设讲,并定期展览科学技术成就。傅兰雅出任书院监督,徐寿为主管。傅兰雅每周亲自到格致书院讲学一次,并编订出矿务、电子、测绘、工程、气机和制造等六种西学课程,他希望使格致书院“成为在中华帝国传播西学的一个中心。”这是中国较早的教授西学的近代学校,也为近代中国新型学校的兴起起了示范作用。
1876年2月,傅兰雅自费创刊了科学杂志《格致汇编》(The Chinese Scientific and Industrial Magazine)期刊,自任主编,这是中国第一份科技杂志,所刊多为科技新闻与常识。《格致汇编》于1876年2月9日发刊,至1878年3月,因傅兰雅送妻子回英国治病而第一次停刊;1879年秋,傅兰雅返回中国,第二年,即1880年4月复刊。此次复刊,仍然每月出版一期,直至1882年1月,因亏本较多而第二次停刊。不久,傅兰雅再次将其复刊,并改为季刊,直到至1892年,因傅兰雅赴美参加世界博览会而停刊,此后再未复刊。《格致汇编》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介绍各种科技知识,深受读者欢迎,清末曾一再重印,成为当时最有影响的杂志之一。许多维新派领袖如康有为和谭嗣同等人,皆从该刊获取新知。维新派领袖梁启超在其《西学书目表》中称《格致汇编》为“极要”。当闻知《格致汇编》停刊后,梁氏痛惜疾呼:“今中国欲为推广民智起见,必宜重兴此举。”
五、傅兰雅与“益智书会”
1877 年,傅兰雅应邀参加了基督教在华宣教士组织的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益智书会。1879 年,他被推举为该会总编辑,从事科学普及工作。在他主持之下,至1890年,该书会编印和审定了98种适合作为教科书的书籍和教学挂图,傅兰雅编写和编译的《格致须知》、《格致图说》等科普教科书,在中国早期新式学校中影响很大,有许多被采用为教科书。《格致须知》、《格物图说》和江南制造局等译著,组成了由浅入深的科学译著系列,为当时中国人学习科学知识和了解新思想提供了便利。益智书会在中国约近40座城市有代销点,出版和销售的书籍达千余种,数十万册。
1885年,傅兰雅又在上海成功创办了“格致书室”,是为中国第一个科技书店,不仅销售几百种中外学者的科学技术译着,还代售地图、人物画像、仪器、印刷铜模、印刷机等。三年后,格致书室还在天津、汉口、汕头、福州、香港、沈阳、烟台、厦门和北京等地设立了分销处,这些图书的销售大大促进了科技的传播,格致书室也因此被称为“中国青年学生学习西学的麦加”。
六、创造专门科技术语与字汇
在传播科技的过程中,傅兰雅非常重视科学名词的理论研究。可以说,晚清寓华西人中对科技出版用语的规范化表达关注最多、影响最大的就是傅兰雅了。在为中国设计大船的时候,傅兰雅感到中国没有化学元素的文字,很不方便,就利用他的中文功底,加上他身边的中国助手徐寿等人,把流行于世界的化学元素的拉丁读音,都用中国的汉字的偏旁部首重新组合,形成新的中国专业术语和名词。1871年,傅兰雅和徐寿合译的《化学鉴原》,首次提出一套完整的元素汉译原则,并给出了当时所知的64种元素的汉译表。《化学鉴原》被清末学界奉为善本,其元素译名及“取罗马文之首音译一华字,首音不合则用次音,并加偏旁,以别其类,而读仍本音”之形声字创制原则也广为人知。今天我们所采用的化学元素命名原则便是源自于《化学鉴原》,他们所翻译的如钡、钠、镁、铝、锰、铬等仍沿用至今。他们命名的元素和有机化合物名词在当时是比较特殊的名词,对中国人而言无疑是一种陌生的词汇。而且在17、18世纪,许多西方人士也认为西方的科学知识是不太可能译成汉语的,一是认为中国语言不适于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二是认为中国没有相关的学科和术语体系。然而傅兰雅认为,中国文字和其他文字一样都会成长,中国的语言与西方的语言一样具有强大的活力,其名称术语的构成绝不比西方语言差。他曾用英文来做例子:“必须记住,当英文开始借用希腊文及拉丁文的时候,很多被创造出来的科学和科技名词都是来自于不同的或者已经被其他名词取代的,所以中文也应该被视为那种能够借用英文或其他语言的文字。”傅兰雅认为,汉语特别是书面语具有非常灵活、很强的表达力和极为简练易懂的特点,比世界上其他任何一种语言更容易表达现代科学术语。他说:“中文不仅不存在使西方的科学思想难于表达的问题,而且,与此相反,中文在翻译方面独特的适应性是世界上其他任何语言所没有的。中文书面语特有的灵活性、表达力及简练性,使得它能够广泛地接受或适应外国思想,尤其是外国思想中新生的但极具智慧的科学术语。”因此,只要掌握汉字的构成规则,外来名词加入汉语系统是没有任何困难的。他的自信同样来自于对历史事实的总结,他说:“如果我们观察远自佛教传入以来,或者近自早期耶稣会士东渐以来,所输入的新名词或新概念,我们就会发现那些流传下来的著作里几乎没有什么概念用中文轻易表达不出来的东西。”
傅兰雅认为新术语的创制会丰富汉语语言,赞同将官话作为对译的中文发音标准。傅兰雅讲到“用华字写其西名,以官音为主。”在具体的翻译方法上,傅兰雅倾向于意译或是描述性的解释法。傅兰雅认为描述法(意译法)、音译法以及二者结合的这三种翻译法中,中国人似乎更容易接受採用描述法的翻译,所以“新译名应该尽可能采用意译而不是音译。”而意译和音译二者结合符合中国文字所具有的表意文字的特点,特别是形声字,既能表音,又能表意,所以可以多用此法创制新字。他曾特别提到“袈裟”(Kashaya or Cassock)一词,既体现了原文发音,又通过“衣”字表达了它所具备的意义,是意译和音译的完美结合。而他的元素译名也恰恰是这一种翻译方法的体现。
傅兰雅强调术语厘定和统一的重要性。由于当时译者各立门户,自建术语体系,互不参照,傅兰雅认为科技名词的翻译如不统一,势必使译名混乱,含义难辨。他认为统一译名对译者与读者都大有好处。至于如何统一译名,他主张“凡前人已用者,若无不合,则可仍之,犹之西格致家,凡察得新动物、植物等而命以名,则各国格致家亦仍其名而无想更改者。”这就是说,如同科技名词一般沿用发明(发现)者的命名一样,译名也宜沿用初译者所用的名词,但译名必须合适。他还提出了翻译科技名词的标准,指出:“一个名词是否能够使用下去,全看它在公众评议或使用中优缺点如何。如此名词意义乖误,或易被误解,或使用不便,或表达不当,则终归要被淘汰,而不必问其当初是何人所立的。”傅氏的这段话,包含着翻译科技名词必须词义正确、不易误解、使用方便、表达贴切等几项标准 。在益智书会统一术语的工作会议中,傅兰雅多次提出西学译介者们应该尊重和沿用前人已有的译介成果,他更注重尊重中国的传统和中国人的语言习惯。他的元素译名很能体现他对中国传统的兼顾。在他和徐寿创制的49个化学元素译名中,有21个都是对《康熙字典》里不常用之字的重新启用。“以字典内不常用之字释以新义而为新名”的方法是他十分推崇的。在译事上,他建言:我们必须摈弃西方的特点和习惯。要想让中国人尊重西学,我们必须小心地避免独断专行。在通行性上,我们的体系并不比中国的优越。中文古老而丰富,更有理由成为全世界通用的语言,不应该被引进西学的人任意篡改。这样的言论在当时来讲,可谓是相当大胆而过激的。因为19世纪晚期活跃在西学译介和教育领域的西方人士,多以西方近代先进科学技术的眼光来审视中文和中国落后的现状,大多不可避免地保有一种先天的优越感,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语言和文字是这个国家紧密团结在一起的支柱,是帮助全民族度过灾难的力量,也是中国在历史上称雄邻国的力量源泉,将与国家共存。”
为统一和规范术语和译名,傅兰雅编辑出版了好几种科学术语译名表,计有《金石中西名目表》(1883年),《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1885年),《西药大成中西名目表》(1887年),《汽机中西名目表》(1890年)等,均为现代汉语科技术语学开山之作,其中许多名词的译名比较贴切,一直沿用至今,影响深远。
由于傅兰雅在译述及传播西学方面所作出的重大贡献,清政府授予他“进士”和三品官衔,并颁赐“三等一级双龙宝星”,由此他成为少数几个带有清政府官衔的洋人。为了报答这一切,傅兰雅拼命地工作,甚至不惜付出个人生活的代价。1869年夏天,他的妻子安娜第一次生产时感染伤寒,结果孩子几天后夭折,安娜因过度悲伤,病体一直未愈。
七、培养近代第一批新型的科技人才
傅兰雅在致力于科学技术的普及和传播过程中,有意无意地培养出中国近代第一批新型的科技人才。在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译述生涯中,傅兰雅得到馆内的中西同事,特别是中国笔述者的大力支持。由于当时的翻译是由懂汉语的外国人口译,中国学者笔录而整理成书的。所以,作为翻译馆的主要口译者,他与徐寿、徐建寅、华衡芳、赵元益等人合作翻译了大量的西方科学技术着作,他们志同道合,齐心协力,配合默契,这些人后来都因此而名垂中国近代史册。如翻译馆的徐寿、华蘅芳等人,他们都有中国传统的天算博物之学的基础,通过译书与傅兰雅等西教士朝夕相处,切磋学术,其“格致之学,亦由此益深矣”,水平大有增益,成为清末有数的“格致名家”。徐寿被公认为中国近代化学理论的先驱,其子徐建寅,在科学造诣上,较其父似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参与译书的时候,才20岁刚出头,后来曾作为技术专家到欧洲考察,并在留欧学生众多的福州船政局担任提调,可谓是当时第一流的科技专家,他与李凤苞等“因译书而为官者皆通晓西事,能知中西交涉所有益国之处.”此外,如赵元益、华备钰、江衡、徐华封等人也各有专长。他们的译著还为清末的新式学堂,如武备学堂、矿物学堂、水师学堂等提供了教材。直到20世纪初年,其中的某些译著还被一些专门学堂采用。更令人瞩目者,大批知识分子接受了输入的科学新知识,动摇了中国数千年“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传统价值观念,引起了对封建制度的怀疑和否定,萌生了变革社会现实的愿望和要求,因而成为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先声。
山东学者栾学谦长期被傅兰雅聘为佐理著述,与傅兰雅共同翻译许多著作、文章。作为笔述者,栾学谦在编辑《格致汇编》时,承担了笔录、整理、修改和定稿等大量工作。可以说他所付出的精力、时间和劳动,不亚于傅兰雅。因此他也跻身于晚清一流科学家之列。
傅兰雅尽管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中国的科学技术事业,但由于中国的传统势力太强,进步太慢。所以也有他的苦恼。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最终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之后,傅兰雅说:“外国的武器,外国的操练,外国的兵舰都已试用过了,可是都没有用处,因为没有现成的、合适的人员来使用它们。这种人是无法用金钱购买的,他们必须先接受训练和进行教育。……不难看出,中国最大的需要,是道德和精神的复兴,智力的复兴次之。只有智力的开发而不伴随道德的或精神的成就,决不能满足中国永久的需要,甚至也不能帮助她从容应付目前的危急。”这些话是他在华30多年的深切体会,对今日中国之改革,仍不失为警示之语。
八、倡导与推广时新小说
除了翻译西书、传播西学外,傅兰雅还有另一重要建树,就是倡导和推广新小说。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一时全国群情激奋,改革呼声日高。傅兰雅从中受到鼓舞,大力抨击被他称为危害中国社会、妨碍进步的“三弊”,即鸦片、时文和缠足,并于1895年5、6月份,先后在《申报》、《万国公报》和《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s)上刊登“求着时新小说启”的广告,出资公开举办有奖征文的新小说竞赛,广泛征集抨击“三弊”,提出救治良方的小说。傅兰雅在广告中首次使用了“时新小说”这个术语。1895年9月18日,时新小说有奖征文结束,从全国各地共收到了162份稿件。傅兰雅仔细阅读了所有稿件,并邀请了沈毓桂、王韬、蔡尔康等知名人士参与评选作品。这次时新小说有奖征文比赛促成了一批新小说的出现。不少作品除了对当时的社会弊害进行揭露和谴责外,还积极地设想改革方法,以促进国家的兴盛富强,达到具体教化社会的目标。在这一点上,它们实际上是主张改良社会风气的社会小说,是晚清谴责小说发展的先声,而且它们产生的时间比梁启超1902年发起的新小说运动早了7年,比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早了8年。有学者甚至认为这些时新小说是现代小说的源头和前奏。令人遗憾的是傅兰雅所征得的这162部稿件,在百年间没有一篇得以发表。而且这批从未面世的珍贵文献之下落也长期成为学术界的一个悬案。直到110年后的2006年11月22日,美国柏克莱加州大学东亚图书馆的中文部馆员在图书馆新馆落成搬迁时,在一间堆满书刊杂物的储藏室里,竟无意在两个尘封已久的纸箱中找到了这批时新小说的原始手稿。原来傅兰雅于1896年3月在《万国公报》上刊登出时新小说获奖人名单后两个月就离开上海到美国的柏克莱大学任教,同时,他把在中国收集的私人藏书和手稿一起运到了柏克莱,其中包括他在中国收集的两千多册中英文书籍、一百多部译着和个人档案、手稿等。那时,他已经没有时间把时新小说征文中较好的作品整理刊登出来。他的工作重心已经转到美国。这批时新小说也就被打包,运到太平洋彼岸的柏克莱了。1896年8月傅兰雅开始在柏克莱大学教课,他的私人藏书也被放在校园供他和学生们使用。傅兰雅在去世之前,将他的私人图书馆全部捐赠给了柏克莱加州大学,成了东亚图书馆的第一批藏书,也是早期来到美国的珍贵中文藏书之一。
九、在美国晚年岁月
1896年6月,傅兰雅从上海动身回国度假,抵达美国后,受聘为柏克莱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学教授。原定5个月的假期,一变而成为他永久离开中国的契机,而他在华30多年的事业,也至此画上了句号。至于傅兰雅为何离开他生活了35年之久的中国而去美国柏克莱大学任教,学界有不同说法。有学者认为,傅兰雅离华是对中国感到失望,觉得他本人在中国的努力是个失败。另有学者则认为傅兰雅的离开是出于家庭和经济方面的考虑。从《傅兰雅档案》的傅氏家书中,不难看出傅兰雅离开中国移居美国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家庭的因素。我们可以看到傅兰雅是一个非常爱家、注重孩子教育的人。早在1891年,傅兰雅的第二任美国妻子伊莱莎•尼尔逊(Elisha Nelson)已经携带他的4个子女到加州奥克兰定居。他在1895年1月6日给加州大学董事会写信曾提到这件事。此外在1895年5月22日写给加州大学凯洛格校长(Martin Kellogg)的一封信里,傅兰雅也披露他移居美国的另一原因。此时,傅兰雅已经在上海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工作28年,他觉得翻译西书、传播西学的工作可告一段落,特别是甲午战争的结局使他感到改造中国需要加速,译书费时缓慢,跟不上时代的需要。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学习外国语言,接受欧美教育才有希望赶上邻国。傅兰雅认为中美关系会日益密切,接受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学讲座教席的职位可让他在教授中国语文和文化的同时,尽他一切可能,协助中国学生留美,从而继续帮助中国。
当时的傅兰雅看到了加州大学阿加西讲座教席(Agassiz Professorship position)的重要性。在以上这封信中,他提到了四位可以证明他能够胜任此教席资格的人:他们是牛津大学教汉语的理雅格博士(Dr.James Legge)、英国剑桥大学任教的汉学家威托玛爵士(Sir Thomas Wade)、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博士(Dr. William A. P. Martin)和当时居住在上海的中国文学专家艾约瑟博士(Dr. Joseph Edkins)。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的汉学家。傅兰雅转向学术界,他三十多年的中国经历和知识完全可以派上用场。此外,在加州大学他还可以培养从中国来的留学生,这也是他的心愿之一。这些人将来能够回国去改变中国状况,并应用西方教育体系替代陈旧的中式教育。他后来果然在柏克莱接纳中国留学生,开办中国留学生之家,建立东方学院。他从此迈出了他人生的下一步:从传教士到传播西方科技之火于中国的先知,最终成为一个教育家和汉学家。此后他一直在柏克莱大学,1902年担任东方语言与文学系(Department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in Berkeley)主任;1913年退休,直到1928年去世。在此期间,傅兰雅仍心系中国,多次重访中国。虽然在美国教学任务繁忙,但他仍能够在1896-1909年间,为江南制造局翻译出14本书,平均每年一本。傅兰雅的长子傅绍兰(John RogersFryer)继承他在江南制造局译书,不久病逝于中国。
1911年傅兰雅捐银6万两,建立了上海盲童学校,这是中国的第一所正式的盲童学校。他还专门为盲童教育编译了《教育瞽人理论法》一书,由上海时中书局出版。不久他又捐巨款在汉口建立一所盲童学校。1915年,他在美国家中与前来参加博览会的黄炎培交谈时,充满深情地说:“我几十年的生活,全靠中国人民养我,我必须想一办法报答中国人民。”他特意让自己的小儿子傅步兰(George B. Fryer)在美国学习盲童教育,然后派来中国,担任上海盲童学校校长,并且又建立起一所盲女学校。1926年,傅兰雅还在上海创办了“傅兰雅聋哑学校”,该校于1953年被中国人民政府接管,成为后来的上海市聋哑中学。
1928 年7 月2 日,傅兰雅逝世于美国加州柏克莱城家中,享年89岁。
毋庸讳言,年轻的傅兰雅初来中国时是存有名利思想的,他也并没有想到要以翻译为其终身职业,在写给父亲的信中他如此写道:“我希望以此作为通向更高职位的晋身之阶。”但在他从事译书生涯二十多年后,他再也不做如此想了,再“无藉此求利之意”了。傅兰雅深深感受到科学对于封闭中国的重要性与迫切性,力图通过办报、办学和译述,使中国读者对西方的事情、科学和教育感兴趣,并以此实现他“格致之学得以畅传中土”,“广布西学于中国”的宏愿。他在1892年《格致汇编》停刊时深情地回忆道:“半生心血,惟望中国多兴西法,推广格致,自强自富。”又在《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中说:“余居华夏已二十年,心所悦者,唯冀中国能广兴格致,至中西一辙尔。故平生专习此业而不他及。”长期的中国生活使傅兰雅逐渐改变了原有的名利观,他衷心希望“帮助这个古老的民族走向强盛,使之跨入西方人引以为傲的向‘文明进军’的轨道”(John Fryer’s Calendar,1869)。因此在他创办《格致汇编》时,明确提出了不以赢利为目的:“工资取诸自备,收回售价,庶能补不甚亏。”虽有同事“供给膏火”以及有时登载广告的收入略作补充,但日计月核常常仍是“入不敷出”(《格致汇编》,1876,卷二),偶有盈余,则“多加图说,以增页数”,“本无藉此求利之意”(《格致汇编告白》,1876,卷六)。傅兰雅如此不惜巨金,不计心血,旨在使“格致之学得以畅传中土”,为此他呼吁读者“勿惜百钱之费”购阅此编(《格致汇编》,1877,卷五)。梁启超曾评论道:“闻傅兰雅因译此编赔垫数千金。”(梁启超:《西学书目表•读法》)光绪二年(1876年)正月初十日出版的《申报》评价《格致汇编》:“其价甚廉,其书甚美,其中所言皆属有益于人生之事,中西讲求格致之人所可取法者也。”后又说:“取资以充印费纸本,亦颇廉售,盖意不在逐利也。”(《读(格致汇编)二年第四卷书后》,申报,光绪三年五月二十日,第1589号)
傅兰雅早年在英国,晚年在美国,中青年时代在中国,他将他一生最宝贵的年华献给了中国。他的科学译著和《格致汇编》为封闭、落后的中国开启了近代化之门。他长达20余年的科技翻译和科普工作,为中国产生出一批虽然不多却也引人注目的科技人才。其科技术语的翻译确定原则影响至今;新科学的引进,不但引起了国人对西学的空前关注,最终还引发了教育制度的变革。与他同时代的人称傅兰雅的工作“实为先路之导”(《格致汇编》第二年第十二卷•申报馆稿)。作为一位科普先驱、译书巨擘,傅兰雅传播西学内容之富、范围之广、方式之多,同时代无人可与之比肩。1877年,晚清名臣曾纪泽去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视察工作时,曾赠诗与傅兰雅曰:“君名远迈南与汤,好似电火胜萤光。”(注:“南与汤”即指明清时期的耶稣会士、科学家南怀仁和汤若望) 如果我们对傅兰雅一生的科技传播实践进行综合评价,一定会认同他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确是堪比南怀仁和汤若望的一位重要使者。称他为“西学传播大师”和“传播科技之火于华夏的普罗米修斯”并不为过。
归属
This article is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from A Dictionary of Asian Christianity, copyright © 2001 by Scott W. Sunquist,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Grand Rapids, Michigan. All rights reserved.
资料来源
- Fryer, John, “Science to China,” Nature. 1881.
- Fryer, John, “Scientific Terminology: Present Discrepancies and Means of Securing Uniformity.”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0.
- John Fryer, “The Present Outlook For Chinese Scientific Nomenclature.” Records of the Second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6.
- 傅兰雅,《江南制造总局翻译西书事略》,江南制造局, 1880年。
- 王扬宗着,《傅兰雅与近代中国的科学启蒙》,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年。
- 樊洪业、王扬宗着,《西学东渐——科学在中国的传播》,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年。
- 王淳,“近代西学传播大师傅兰雅”,《信阳农业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年,14(2)。
- 孙邦华,“寓华传播西学的又一尝试——傅兰雅在上海所编《格致汇编》述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5)。
- 杨丽君、赵大良、姚远,“《格致汇编》的科技内容及意义”,《辽宁工学院学报》,2003,5(2)。
- 王扬宗,“《格致汇编》与西方近代科技知识在清末的传播”,《中国科技史料》,1996年。
- 范守义,“定名的历史沿革与名词术语翻译”,《上海科技翻译》,2002年,(2)。
- 袁锦翔,“晚清杰出的科技翻译家傅兰雅”,《翻译通讯》,1984年,(2)。
- 朱振华,“傅兰雅与西学东渐”,《南开史学》,1984年,(2)。
- 孙邦华,“傅兰雅与上海格致书院”,《近代史研究》,1991年,(6)。
- 徐振亚,“傅兰雅与中国近代化学”,《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2)。
关于作者
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