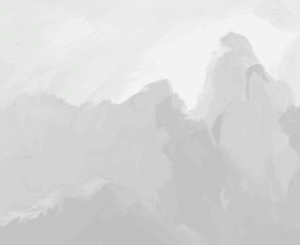一、早年生活与神的呼召
华理士(William Wallace)于1908年1月17日生于美国田纳西州诺斯威尔城(Knoxville),父亲是一个内科医生。在他11岁时,一场流感夺去了他美丽贤淑的母亲,剩下父亲和外祖母照顾他和妹妹。他具有机械方面的秉赋,当其他同龄人开始醉心于体育、学业或社交之际,他却埋头钻研机械,而且小有成就,因此他的亲朋和家人都认为他将来必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工程师。然而,在华理士17岁时的一天下午,一向沉静寡言的他却怎么也定不下心来做他喜爱的机械活计,仿佛内心有一股力量在不停地催迫他,让他停下手上的工作,静下心来认真思考生命的意义。一个问题不断在他脑海中浮现:“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么?”就在那一瞬间,华理士似乎清楚地听到了神对他的呼召——“准备当一名宣教医生,将来到我差遣的地方去传福音!”1他随即拿起打开的圣经,在页边的空白处写下了自己对神呼召的回应。当时他并不知道日后神将会差遣他到哪里去,但从那一天起,他就决志奉献自己为主所用,定意要做一名医疗宣教士,并开始努力装备自己。
高中毕业后,华理士进入田纳西大学医学预科,后在孟菲斯大学医学院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在诺克斯维尔总医院实习期满后,留在该院担任外科住院医师。但就在他医学院毕业时,他的父亲去世了,家中只剩下他和妹妹路德两人。
华理士生性腼腆,自己认为口才不好,不适合作教师。但他对宣教事业充满热忱,确信神将使用他作为一名医疗宣教士。他是一位和蔼、诚恳的青年,常常是在幕后默默工作,但在他柔和谦卑的表现背后,却有着一股很强的内在吸引力。1934年,华理士26岁,在诺克斯维尔总医院作外科医师时,他写信给美国南方浸信会海外传道总部,要求成为一名医疗宣教士,到有需要的地方去为主服事。奇妙的是,就在同一时刻,另一封来自中国广西梧州的求助信也寄到了总部。由美南浸信会创立的思达医院(Stout Memorial Hospital)院长毕济时医生(Dr. Robert E. Beddoe)向总部呼求,急需一名传教医生,而且一定要是外科医生。因他罹患眼疾多年,已无法做外科手术,希望一位医生能来接替他。毕济时在信中代表那些在梧州所有饱受痛苦煎熬的病人呼求,请差派一名外科医生来思达医院。这两封信同时寄到总部,从中可见神的旨意。
就在华理士开始准备去中国医疗宣教之时,却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另一个颇有吸引力的邀请。他父亲的老朋友,美国外科医师学会一位资深会员邀请他来合作,成为行医的合伙人。华理士很清楚这个邀请对自己将意味着优厚的高薪、医学界“最前沿领域”的地位,以及前途广阔的职业生涯等,这些都是一个年轻住院医生梦寐以求的。这突如其来的大好机遇,对华理士来说是一个大诱惑。在其后的几天里,他一直为此事祷告。毕济时医生从广西梧州给他寄来的那封信,一直在他脑海中:“我一直恳求总部派一名年轻外科医生来,看来你可能就是担当这个岗位的人选了。我盼求并祈祷这一愿望得以实现。你的牧师极其热情地写信推荐你。如果你就是主所选定的那一位,我祈祷你能尽快到来。时间不多了,我们当趁着白昼,赶快作工。关于这里的现状,我可以足足写上几个小时,相信这样或许更容易激励你作出决定,但我的时间有限,而且我也不愿意过于勉强你。我只能说,对于一个愿意点燃自己生命去荣耀神的人,这实在是一个最不寻常的开端。我盼望你就是那一位。”2几天之后,华理士再次来到老前辈的办公室,把自己准备当宣教士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和盘托出。作为晚辈的华理士带着他那为人所熟悉的腼腆神情,婉转地谢绝了父亲老朋友的盛情好意。
二、在梧州思达医院之岁月
1935年,27岁的华理士辞别家乡,坐上“柯立芝总统号”远洋海轮踏上了去中国的征程。他终于看到了神在他生命中的安排——医生、宣教、中国。到达中国后,华理士先在广州学习一年语言,之后立刻开始在梧州思达医院的医疗工作。虽然他在语言方面还存在一些困难,但他总是尽最大的努力学习,在行医、拜访病人时,尽力用粤语与人沟通,并以极大的热心和真诚从事医疗事业,在很短时间内便给医务同仁和中国病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毫不造作的微笑、以及对他人真诚的关心,迅速赢得了大家对他的尊敬。
华理士的日常工作非常忙碌,每天一早起床,他便开始早晨的灵修,翻开圣经,选读其中的几页,在心中默记经上的内容,最后低头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之后他就去病房查房,察看夜班记录,指导助手的工作。在吃早餐之前,通常先安排一个手术,如果是一般的小手术,就连做几个。与在家乡不同的是,现在他必须独当一面,经常会遇到以前从未见过的病例,需要处理许多以前他未曾处理过的难题。他给病人摘除过体积庞大的肿瘤,做过极其精细的眼科手术,缝合兔唇、腭裂等手术更是家常便饭;还有阑尾切除、截肢、妇科难产手术等等。华理士用他的手术刀救治了无数的病患,在医治患者身体的同时,也关心他们的心灵。虽然他的粤语还不流利,但关怀体贴不一定非要靠语言来表达。华理士常常向病人和他们的家属讲述耶稣基督的救恩,他怀着同情和怜悯的心,告诉他们,主耶稣爱世上每一个人。“华医生”的名声迅即在广西当地传开,许多病人慕名远道来思达医院专门找他求诊。许多在梧州的人说:“我们在他以前听过很多讲道,但是通过华医生和他所做的,是将其活了出来,我们看见了信仰的真谛。”3自从华理士到来后,思达医院的病人增加了百分之五十。医院员工灵性也得到复兴。许多人得救归主,其中有两个家庭是全家得救,一些医生也加入了教会。当时有两位华人医生公开受浸,认信耶稣基督为救主,这在当地并非易事。因为他们必须要打破本地千百年来拜偶像的传统恶俗,承受来自家庭和社会各方的巨大压力,但这也体现出神的权能。宣教士在梧州布道多年,基督教会在当地也已经建立多年,许多与宣教士一起工作的华人,不是没有机会听闻福音,但他们从华医生的身上,真切地看到了基督徒应有的样式。华理士虽然讷于言辞,粤语也说得很蹩脚,不能滔滔不绝地当众讲道,但他的行为却起到了主耶稣所说的“光与盐”的作用,无愧于他作为一名宣教医生的神圣职责。忙碌的工作对于华理士来说,是一件令他兴奋的事。每当看到病人痊愈,他就感受到被主所用的喜乐,享受到圣经所说的“福杯满溢”的感觉。
华理士在梧州的时期,正是日军侵略中国之时,梧州城经常遭到日军飞机的轰炸,很多时候华理士的手术是在轰炸中完成的。一次手术进行到尾声时,突然遇到日军飞机的轰炸,转移病人已经来不及了。华理士果断命令所有人立刻离开去防空洞避难,由他一人结束手术。中国医生和护士离开后,华理士独自完成手术后的所有收尾工作,随即把病人推到一间没有窗玻璃的大房间。这时病人清醒过来,被身边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吓得魂飞魄散,华理士伏下身把他按在床上,用自己不太流利的粤语尽力安慰他。日本军机飞走后,医护人员立即从地下室冲出来,飞跑到刚刚落下炸弹的顶楼。他们惊喜地看到,华医生和刚刚做完手术的病人正在房间里一起祷告。
在毕济时院长去支援桂林的浸信会医院时,华理士担负起思达医院院长的职务。1944年,梧州被日军占领前,医院不得不疏散。医院55位医护人员停工,将医院所有物资都转移到驳船上,成为了一间“走动的医院”。在华理士领导下的思达医院,在战火中先后辗转藤县、桂平、百色、南宁等地,历时长达一年之久,经受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苦艰险和生死试炼。一位信徒对华理士说:“我们就像当年摩西率领以色列民出埃及过红海后在旷野跋涉一样,白天有云柱,夜间有火柱。”4在疏散途中,他们面对严重的食物短缺,华理士反复鼓励大家要沉着镇定,藉着祷告安稳众人软弱的心。同时,他也费尽心思四处寻找粮食,按各人所需进行定量配给,并对患病的同工给予特别照顾。一位护士后来忆述:“有一天华医生又把自己的那份米饭让给了生病发烧的护士吃。饭后我走出来,没想到无意中却发现他躲在帐篷后面,正偷偷地把烧糊扔掉的饭焦捡回来塞进嘴里。他看见我后,顿时显得很不自然。我相信,平常习惯吃牛奶面包的华医生并不是因为吃饭焦而难为情,他是不想让人知道他其实饿得有多厉害。他瘦得像根禾杆,看上去一阵大风都可以将他刮跑。”5奇妙的是,华理士没有因长期饥饿和日夜操劳而倒下,反而时刻展现出一种令人佩服的非凡毅力和坚定信心。他千方百计地想办法给大家补充营养,例如找来一些禽鸟的骨头捣烂煮着吃,说这有利于增加维生素。思达医院的许多医护人员就靠这样的方法维持生命,度过疏散转移过程中最危险的难关。
三、为爱失去良伴
1940年,华理士第一次回国休假期间,在一次浸信会例会上遇见了一位秀外慧中的年轻女子,她是浸信会差会总部的一名职员。早在1935年华理士来总部接受差遣时,她就见过他了,并且对这个蓝眼睛的瘦高腼腆的小伙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更巧的是,女孩的父母曾经在中国宣教,她本人就是在中国出生的。这因缘一下子就把两人的距离拉近了。会上他们常常坐在一起,亲切愉快地互相攀谈。华理士一反平常寡言少语的态度,把她视若知己,将自己在中国几年的所历所闻,以及在宣教事奉工场中遇到的种种困惑和苦恼,都向她一一倾吐。华理士登门拜访了这位年轻姑娘和她的父母,大家一起在家里吃了几顿饭,畅谈各自在中国事奉的经历。彼此的了解和友情都更加深了。华理士离开后,两人开始频繁地互通书信。华理士的休假结束前,他再次专程看望女友。他们一起漫步攀谈,大部分时间是华理士一个人在说,姑娘在身旁静静地听。年轻医生所谈的,依然是他在宣教事奉中的种种感受。但直到最后在火车站挥手告别的那一刻,华理士都没有对女友说出半句求婚的话,他只是请对方给他写信,并承诺在几年之内会再来看她。当妹妹问起时,华理士说:“我喜欢她,也许真的应该娶她,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没能这么做。我想过,现在这个时候,怎么能带一个女孩到中国去?很不安全,那里正在打仗啊。”6
四、不断进取,轻看荣誉
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华理士抓紧一切时机学习科学知识。他利用短暂回国休假的时间装备自己,进修与外科有关的课程,除了听课、做实验和临床诊病之外,每天晚上他都到医学图书馆阅读专业刊物,直到闭馆的时间。他这样作是为了更好地服事在中国的病人。他经常告诫手下的医护人员,医学发展永无止境,无论哪一个医生都不可以自满而停止学习。1947年5月,即将结束第二次休假的华理士正在诺克斯维尔的家中收拾行装,准备两天后前往旧金山搭乘开往中国的海轮,忽然接到一位好友的电话:“威廉,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你已经获选为国际外科学会(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Surgeons)的会员了。”7华理士听了大感诧异。他在中国工场事奉了十二年,一直在梧州思达医院默默无闻地埋头工作,虽然亲手医治过数以万计的病人,但从来没有参加过什么国际学术会议,也没有发表过什么医学论著,怎么会有机会获得这么高的学术荣誉呢?想当年,他谢绝父亲的老朋友诚意邀请,放弃加入医务所的难得机会,义无反顾地奔赴万里之外的中国福音工场,就已经没有在学术界出人头地的任何念头和打算了。正因为华理士用自己的方法所做成功的临床手术的数量,是许多美国的同行无法相比的。他完全配得这份荣誉。但华理士并没有太多的欢喜,相反,他更加谦卑在神的面前,在满怀感恩的同时,更加迫切地意识到神呼召他的使命尚未完成,要“趁着白昼,赶快作工。”他从没向任何人提起这件事,直到梧州的某位同工有一天偶然意外地发现此事,大家才惊喜地知道,身处中国西南一隅、还不到40岁的华医生,其精湛的医术已经获得国际医学界的公认,达到了国际级的高水准。虽然他的医术广受赞誉,但他从没有忘记自己是一名担负大使命的宣教医生,他的职责不仅仅是治疗人们身体的疾病,更要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让人认识这位救赎万民的全能者。回到中国后,他把诊症、开药、做手术,都看作是传福音的机会。除了医疗治病,他也常常组织宣教队伍到周围乡村去进行医疗旅行布道。
五、深得民众喜爱
抗日战争后的思达医院,是一片颓败荒废的景象。华理士院长看到周围都是病人,需要医院。在他身先士卒的带领下,思达医院的修复和重建工作逐步恢复。短短一星期后,在医院五楼弹痕累累的小礼拜堂内,全体同工举行了庄严隆重的崇拜,众人在神面前再次坚定自己奉献的心志。礼拜结束后,大家一起下楼,来到前院,打开医院的大铁门。被迫关闭整整一年的浸信会梧州思达医院正式宣告重开。
1948年夏天,梧州爆发流行性副伤寒,日夜接触病人的华理士也不幸感染了病菌。开始时他还能向其他医生发出医嘱,但后来病情逐渐恶化,持续高烧导致他神志不清。思达医院的华人医生们心急如焚,竭尽全力施行抢救。陷入昏睡中的华理士不时发出呓语,如果高烧一直这样持续,后果不堪设想,但该用的药物都已经用上了。伤寒是致命的传染病,此时,医生们似乎已经束手无策了,唯有仰望神的大能之手施恩拯救。医院楼下的院子里聚集着一大群人,静静地站在医院大楼前面。他们当中有做买卖的、干苦力的、讨饭的、当小职员的;有基督徒、也有未信主的,全都通宵达旦一直守候在那里。自从华医生病倒的消息传开后,每天都有大批梧州民众来到思达医院探望。由于华理士被隔离在传染病房,他们无法亲眼见到敬爱的华医生,便日夜守候在住院部的大门前,焦急地等候着院方报告华医生的最新病情。各地教会的信徒都在牧师和传道人的带领下,和思达医院的全体同工一起,同心合意地为他们所爱的华医生恳切祈祷。两位美国医生专程从广州乘汽船赶到梧州参加会诊,但除了给病人输血和输液之外,他们也没有其他办法可想。守候在医院大楼前的群众越来越多,虽然没有听到华医生病情好转的报告,但只要华医生还有一口气,大家就仍然坚持守候着,仍然抱着希望。终于几天后,他的体温开始下降,当医生过来仔细探过华理士的前额和双手后,高兴地证实他的烧退了,挺过来了。喜讯立刻传到楼下等候的民众,人群中顿时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欢呼声——华医生有救了!
六、为主殉道
抗日战争结束后,平静安稳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多久,国共内战便全面爆发。到1949年开春,时局日渐紧张。梧州的宣教士们接到在广州的美国领事馆发出的通知,建议所有美国人尽快离开华南地区。华理士和女传道古姑娘(Miss Jessie Green)、护士长希姑娘(Miss Everley Hayes)决定留下来。他们深信,在战乱的苦难当中,民众更需要来自耶稣基督的平安信息,也需要教会开设的医疗救助服务。随着新政权对教会事工的限制越来越严,许多福音布道工作已经无法继续,女传道古姑娘在中国信徒的劝说下决定离开。这样,只剩下华理士和希姑娘两人留在梧州。1950年12月19日子夜时分,一群解放军士兵闯进思达医院,将包括华理士在内的全体医护人员和职工驱赶到医院的一个大房间里。声称思达医院是一个特务窝点,而华理士就是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到华南地区的间谍头目。华理士面对指控平静地开口说:“我们没有伪装什么。我们本来就是医生、护士、职员,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这里救治病人,并没有其他的目的。”8 但他们声称有证据,诬陷他藏有枪支,以间谍罪逮捕了华理士。
华理士27岁来到中国,十多年来一直以宣教医生的身份在梧州思达医院服务当地的百姓,虽然多次经历战乱和灾荒中的各种危难险境,但被当局作为囚犯监禁,却是他平生第一次。他的中国同工们也没有想到,这竟是一场生死试炼。除了审讯者,没有人清楚华理士近两个月来在狱中的真实处境,因为当局不准任何人去监狱探望他。据曾经与华理士一起被囚禁而后来获释的天主教传教士事后透露,在关押期间,他们见到华理士每天从早到晚所面对的,就是不停的审问、指控、逼供、和批斗,受尽无休止的威吓、谩骂和侮辱。他被洗脑、被要求认罪,他尝试为每一次的审问准备自己,但审问却一次比一次更加严苛,他有时甚至痛苦万分到大哭。肉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令华理士的身心饱受摧残。他只剩下他的信仰可以坚守着。毫无疑问,他的内心经历着极大的痛苦争战。同监的人有时听到华理士在深夜高声呼喊,有时又听到他不断地用力捶打牢房的墙壁。每当这个时候,就见到看守怒气冲冲地跑过来,隔着牢房的铁栏拿木棍猛捅华理士的身躯,直到他失去知觉。华理士在牢狱中被迫害51天后身亡。死后当局硬说华理士是自杀,让同监牢的两位外国神父看华理士吊在房梁上僵硬的遗体,并要求这两位外国神父在证明华理士自缢身亡的文件上签名。但他们不肯写这样的证词,因为并没有亲眼目睹华理士自杀。经过一番争执,最后他们只同意在一份说明在现场所见情况的文件上签了字。当局也不准思达医院的医护人员进入死者“自杀”的现场,更不允许验尸。当华理士的遗体被抬出来时,工友没有看到任何自缢致死的表面征状,也无法看出是否有绳索的勒痕。在更衣时,却发现华理士的上身满布瘀伤。看守们把华理士的遗体放进一个简陋的木棺,随即用铁钉把棺盖钉严封死。在几个士兵的严密看护下,思达医院的几名同工把棺椁抬上一艘小船,顺流而下到达西江边一座小山岗上的墓园内。一个墓穴已经挖好。由于不准举行教会的安息告别礼,同工们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送别他们亲爱的华医生。没过多久,梧州的基督徒冒着极大的风险,自发为他们所敬重的华医生修建了一块石碑,碑身上庄重地刻着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一节的一句经文﹕“我活着就是基督。” 从遥远的美国来到梧州思达医院事奉的华医生,效法了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毕生为主而活,并为主把自己的生命献上,成为了活祭。
华理士自从奉差遣到梧州思达医院担任宣教医生后,16年间仅回过家乡两次。他没有结婚,没有儿女。但他的事迹传遍美国各地和各教会,各种纪念活动持续不断,华理士的精神激励了无数后人去承继他为之献身的福音事工。
脚注
- Jesse C. Fletcher, Bill Wallace of China, 1963, p.3-4
- Ibid, p.11
- Ibid, p.29
- Ibid, p.90
- Ibid, p.96
- Ibid, p.71
- Ibid, p.107
- Ibid, p.145
资料来源
- Jesse C. Fletcher, Bill Wallace of China. (Nashville, TN: Broadman) 1963.
- “中国的华医生”,载《生命季刊》第55、56、57、58、59期;2010年9月、12月、2011年3月、6月、9月。
- 裴斐,“华理士是谁呢?”载《台湾浸信会神学院院讯》,第166期,2007/9/27。
关于作者
作者系美国加州基督工人神学院教牧硕士班学生,在李亚丁博士指导下撰写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