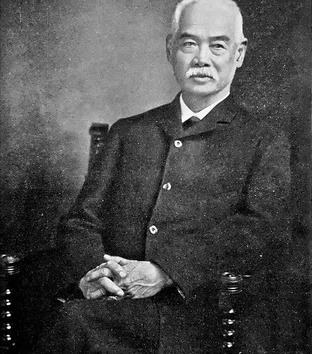容闳,字达萌,号纯甫,1828年11月17日出生于广东省香山县(今珠海市)南屏镇。1835年,容闳7岁时,父亲将他送往英国宣教士郭实腊夫人(Mrs. Gutzlaff)在澳门所创办的一所女子学校读书,成为该校附设的男生班学生之一。1840年,学校关闭,容闳回到家乡。1841年,英国宣教士合信医师(Benjamin Hobson)受郭实腊夫人之托,送容闳到马礼逊学校读书。翌年,容闳随该校搬到香港。
1847年,马礼逊学校的校长布朗牧师(S. R. Brown)因健康原因回国,带容闳、黄胜和黄宽去美国。容闳先入马萨诸塞州的孟松学校(Monson Academy)读书,在此期间,他接受了基督教信仰,成为公理宗教会的一名信徒。他原打算在美国学习二年,但两年后他决定留下来继续到耶鲁大学攻读。
1850年,容闳入读于美国耶鲁大学,成为耶鲁大学唯一的中国学生。读书期间,他认识到西方文化、科学和宗教对中国走向富强的重要性,也一心想将来报效祖国:“我既远涉重洋,身受文明教育,就要把学到的东西付诸实用。……我一人受到了文明的教育,也要使后来的人享受到同样的好处。将西方学术成果引入中国,使中国一天天走向文明富强。这将成为我毕生追求的目标。”1在耶鲁毕业前夕,容闳曾手书孟子的“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1854年容闳获文学士毕业。当时他并不想马上回国,因为几年的美国生活已使他改变许多,而且他业已于1852年加入美国国籍。但就在此时,圣经中的一段话提醒了他:“人若不看顾亲属,就是背了真道,比不信的人还不好,不看顾自己家里的人,更是如此”(《提摩太前书》5章8节)。于是他毅然乘船回国,在海上航行151天之后,经香港回到故土。2
1855年,容闳回到中国。先学习六个月的汉语之后,进入商界充任翻译之职。先后在广州美国公使馆、香港高等审判厅、上海海关等处任职,后在上海宝顺洋行经营丝茶生意。此间,他广交政界和商界的朋友,接触清廷高层人物,以影响朝廷同意其派送幼童赴美学习之计划。
出于对太平天国的同情,容闳于1860年到太平天国首都天京(今南京)拜访了干王洪仁玕,向他提出组织良好军队、设立武备学校及海军学校、建立有效能的政府、以及颁定教育制度等“治国七策”。洪秀全授予他一枚四等爵位的官印,但容闳坚辞未受。同年容闳还随同两位美国传教士到天京游历,进一步认识了太平天国运动。
自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逐渐认识到“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重要性,开始以不同方式引进、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以使中国走上自强之路。清廷重臣曾国藩和李鸿章等人大力支持将幼童送往海外学习,将此视为自强运动的一部分。1863年,容闳奉曾国藩之命,到美国购置机器,以装备洋务派在上海创办的西式机器厂——江南制造局。容闳不负所托,于1865年圆满完成使命回国后,经曾国藩向朝廷举荐,被封为五品官职。
1868年,中美两国签定了互惠协议,允许中国学生到美国任何公立学校读书。1870年,容闳起草了关于幼童留学教育方案,呈送朝廷,为曾国藩和李鸿章所采纳,并付诸实施。在此之前,容闳的幼童留学计划已被朝廷中的保守派阻挡了七年。1871年,清政府最终批准了中国幼童留美教育计划,设立中国教育使团(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原称“幼童出洋肄业局”)。当容闳听到这一消息后,非常激动,整整两天不吃不睡,“他兴奋地走来走去,心中默默地赞美上帝。从他返回中国算起,已逾十六载,上帝终于应允了他的祷告。” 3
清政府在上海为留学幼童设立了预备学校,由容闳负责招收学生,进行强化训练。 1872年夏,首批30名学生乘船前往美国,其中百分之九十的孩子来自广东。他们抵达旧金山后,转乘火车前往康奈狄克首府哈特福德市(Hartford),到站时受到美方接待家庭人们的热烈欢迎。此后他们分住在当地美国人家庭里,提高自己的英语和适应新生活的能力。容闳被任命为留学事务监督,长期驻美,专管留美学生事务。他将中国教育使团设在了马萨诸塞州春田市(Springfield, Massachusetts),并在哈特福德建立一个办公室。学生们通常在假期被召到那里学中文,或为不当的行为受惩罚。
1873年,李鸿章差派容闳和陈兰彬(教育使团督办)分别前往秘鲁和古巴考察中国苦力的生活状况。容闳赴秘鲁进行为期三个月的考察后,向清政府呈交了一份报告,并附上二十几张照片,忠实反映了中国苦力在秘鲁的悲惨生活。于是,清政府根据他的考察报告和照片,不再允许中国劳工前往秘鲁和古巴务工。1875年,陈兰彬和容闳被任命为中国对美国、西班牙和秘鲁的外交特使。身住华盛顿的陈兰彬成为中国驻美国的公使,而身在哈特福德的容闳则为副使,仍主持中国教育使团的工作。
1875年,容闳与当地一位名医的女儿,玛丽·凯劳格 (Mary L. Kellogg) 结婚,由推切尔牧师(Rev. Joseph Twichell)为他们主持了婚礼。事后,推切尔牧师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这是一个美好的结合。有些人对此持怀疑态度,有些人全然反对,还有些人(像我本人)对此则赞不绝口。我认为,只要这桩婚姻不会在中国给容闳带来任何伤害,也不妨碍他对事业的追求,那么,这就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 4
婚后,容闳夫妇共育有二子,长子名叫马礼逊(Morrison Brown Yung),次子名叫巴特莱特(Bartlett Yung,容觐槐)。这两个儿子后来皆回到中国定居,并娶中国女子为妻。马礼逊于1934年死于北京,巴特莱特生活在上海直到1942年。
这些留美学生每礼拜天跟随接待他们的家庭成员去基督教堂,参加教会的崇拜、主日学和查经班等各种聚会,久而久之,有些学生成为基督徒,容闳的侄子容揆就是其中之一,后来他们还成立了“中国基督徒宣教会”。1884年,容揆被任命为在华盛顿的中国公使馆秘书,为国效力达五十年之久。
从1872年到1875年,清廷先后共派遣120人出洋留学,每年派遣30人。但中国幼童留美教育一事,一直为清朝廷中那些保守派官员们所反对。随着反对势力逐渐增大,迫使李鸿章不得不撤回对留学教育使团的支持。虽然耶鲁大学校长与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等人联名写信给清政府;美国总统格兰特也致函李鸿章,指出放弃留美教育,召回中国学生一事是个错误,但皆无济于事。1881年6月8日,清政府下令撤除留美教育使团,命令所有留美学生尽快回国。
1881年8月,几乎所有的学生不得不中断他们在美国的学业,乘船返回中国。其中只有十个学生拒绝回中国,后来他们有的做了工程师,有的从事金融工作,还有的当了中国公使馆的翻译。而回国的学生们却受到空前的冷遇,他们多被安排在很低的职位上,使他们无法发挥自己的作用与影响。在一封给巴特莱夫人的信中,留美学生黄开甲写道:“我们像是一株株幼小的树苗被从水土丰沃之地移栽到愚昧和迷信的干涸荒漠。我们的生命在慢慢地枯萎。” 5容闳为这些学生们的前途和命运四处奔走呼号,希望能帮助他们从“这种粗暴无礼的待遇中解放出来”,但最终还是以失败告终。幸运的是,李鸿章看到学生们的潜力,并将多人从困境中解救出来。有些学生被送到天津的一些技术学院,如电报学校、海军学院和鱼雷学校继续深造,还有一些被送到天津北边的煤矿作监督。渐渐地,一些开明的总督和巡抚开始延揽这些年轻人管理涉外关系或者帮助工矿、铁路和电报方面的事务。事实证明,留美学生们忠于自己的国家,为中国走上自强之路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成为中国近现代外交、铁路、采矿及军事等领域的先驱。他们中有“13人就职于外交领域;6人将大半生奉献给开滦煤矿的管理事业;14人成为中国铁路系统的总工程师或高级管理人员;17人受命于中国海军,其中7人战死疆场,2人担任海军将领;15人成为政府电报局官员;4人从事医疗行业;3人投身创办中国最早的大学。” 6 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外交官唐绍仪、刘玉麟;中国铁路之父詹天佑;香港政府香港行政局首任华人官守议员周寿臣;首任清华大学校长唐国安,以及天津北洋大学校长蔡绍基等。
1883年,容闳回美国照顾自己的妻子。1885年冬,容夫人病情恶化,终于在1886年5月辞世。容闳事业失败之后又痛失爱妻,心灵上的伤痛难以言表。然而,两个儿子却给了他很大的安慰。容闳在自传中写道:
“她的去世使我晚年倍感虚空,一切又是不可挽回的。可是,她并没有撇下我一个人,让我形单影只地度日,而是给我留下两个儿子,他们总让我想起妻子美好的生命和品德。在我日渐衰老的年月中,他们是我最大的慰借。他们富有爱心,情感丰富,非常值得信任,我为他们男子汉的气质和敬虔的品格感到骄傲。我为上帝赐给我这样两个儿子而感恩,愿我的感恩上达天庭,成为我所献上的馨香之祭。” 7
1895年,容闳再度被召回中国,推切尔牧师和夫人将容闳的小儿子巴特莱接到自己家里照顾,直到他从高中毕业。容闳在其自传中表达了他对推切尔一家的感激之情:“这仅仅是他们为避难山教区内外的人们所做的许许多多事情中的一件,但从中我们不难看出推切尔牧师夫妇高尚的品德和博大的胸怀。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让我和儿子巴特莱深受感染 ……。我要重回中国,相信儿子们会得到细心照料,他们的品格建造也必由上帝眷顾。” 8
这次回国后,容闳先去拜见了总督张之洞。之后去上海,试图实施开设银行和修建铁路的计划,皆因国内贪污腐败,和国际局势紧张而以失败告终。其后容闳结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积极参加维新派的活动,支持年轻的光绪皇帝进行变法维新。1898年,慈禧太后发动政变,下令囚禁光绪皇帝,逮捕维新派。为逃避缉捕,容闳躲入上海的外国租界区,旋即又逃到香港。1900年,唐才常的自立会在上海改称“中国国会”,容闳被推为会长,并负责起草英文对外宣言。自立军起义被镇压时,容闳再遭清政府通缉,辗转流亡美国。
1898年,容闳回到美国,受排华法案的影响,颇受歧视。1903年,梁启超游历美国时,特别拜访了处于半退休状态的容闳。日后梁启超在日记中写道:“他已经76岁了,依旧精力旺盛如昨。他的内心充满了对祖国的关心。在两小时谈话中,他就中国的未来给予我很多的教导和鼓励。关于政治,他既理性又思路清晰,令我十分钦佩。” 9
1909年,中美达成协议,将部分庚子赔款用于派遣留学生到美国学习。看到中国学生再次留美接受教育,容闳欣喜万分。1909年8月,在哈特福德召开的中国学生同盟的年会上,容闳鼓励学生们说:“要立志将中国建成领先强国,以改变世界的命运。” 10
容闳于1909年在美国推出其英文版自传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1915年恽铁樵和徐凤石将其翻译成中文,名之为《西学东渐记》。
容闳在逃亡期间结识孙中山,转而积极支持孙中山革命,拥护共和。辛亥革命成功后,1912年1月,容闳致函祝贺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邀请容闳归国效力新政府。奈容闳已力不从心,于1912年4月22日,容闳在哈特福德住所内病逝,享年84岁。老朋友推切尔牧师在避难山公理会教堂为他举行了追思礼拜,将其安葬在哈特福德的柏树山墓地。
1998年,在容闳诞辰170周年之际,耶鲁大学所在的康涅狄格州宣布,将9月22日(当年首批中国幼童入美留学之日)公定为“容闳及中国留美幼童纪念日”。
容闳惟一健在的孙子容永成是容闳的长子容觐彤的儿子,一生做会计工作,如今在上海跟随女儿一家生活,安度晚年。容闳次子容觐槐育有一子二女。大女儿容文真叶落归根,于2004年从美国回到祖父的家乡广东省珠海市南屏镇,入住珠海市慈安护老中心安度晚年。
脚注
- Mark Thomas E. La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Educational Mission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72–1881 (Pullman: Washingto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87), 40.
- Rev. Joseph H. Twichell, “An Address by the Rev. Joseph H. Twichell, Delivered before the Kent Club of the Yale Law School, April 10, 1878,” in Yung Wing, My Life, 247–73.
- Twichell, “An Address,” in Yung, My Life, 270.
- Twichell, “An Address,” in Yung, My Life, 252, 254; La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42.
- Wong to Bartlett; Jerome Ch’en, “The Uprooted,” Etudes Chinoise [Chinese studies] 4, no. 2 (Autumn 1985): 75.
- La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65, 77–78, 107–8.
- Robinson, “Senior Returned Students,” 20; Yung Shang Him,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225; LaFargue, China’s First Hundred, 222–23.
- Ibid., 227–28.
- Worthy, “Yung Wing in America,” 286.
- P. W. Kuo, “The Academy,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The Chinese Students’ Monthly(December 1910): 181–82.
资料来源
- Hamrin, Carol Lee, with Stacey Bieler, ed., “Rong Hong---Visionary for a New China” in Salt and Light,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 2009. Pp. 13-29.
- 网络有关资料。
关于作者
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