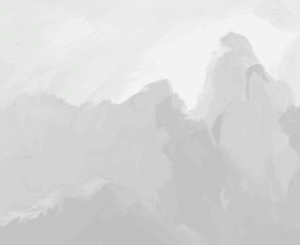五、外交家和驻华大使
从燕大建校到抗战胜利,中国时值兵荒马乱之年代。为了让燕大能够在内忧外患中生存下去,司徒雷登时时关注着中国国内外政治与时局的发展,因此与中国政坛风云人物的接触也日渐频繁。早在1927年9月,国民政府宣布定都南京后,司徒雷登即造访南京,目的是确认新政府对教会学校的政策。经孔祥熙介绍,他结识了蒋介石夫妇。此后他在更多的机会和场合接触、认识了汪精卫、李宗仁、宋子文,以及上海市长吴铁城等政要,请他们帮忙、捐款,帮助燕大度过一个个难关。同时他也在他们中间穿针引线,致力于他们之间的和好与团结。宋美龄甚至把他看为自己的牧师,向他倾吐自己在婚姻生活中的烦恼。周恩来是他所认识的第一个中共领导人。这些都为司徒雷登日后登上政治舞台奠定了基础。
正当中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之日,司徒雷登的人生轨迹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1945年秋天,在燕京大学开学前一个月,司徒雷登前往重庆,出席庆祝抗战胜利招待会。在那次招待会上,他第一次见到了前来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和董必武等人。毛泽东热情地与他握手,口称“久仰,久仰”,然后告诉他说在延安有许多燕大的学生,并夸赞道“你们燕京的学生在我们那边工作得很努力。”当晚,他和毛泽东说古论今,展望未来,谈得十分融洽。9月19日,在燕大校友,周恩来的英文秘书龚澎和她丈夫乔冠华的安排下,毛泽东和周恩来设午宴款待了司徒雷登。在谈到中国的前途时,司徒雷登对未来的和谈寄予厚望,认为“只有和谈成功,中国才有希望。”毛泽东当即建议司徒雷登到延安去看一看,司徒雷登亦欣然表示接受,只是当时因身体欠佳而未能成行。
11月下旬,司徒雷登去美国为燕大募捐,第二年4月回到中国,顺便去南京拜访了相识多年的蒋介石,并在那里见到了作为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负责调停国共两党纠纷的马歇尔。司徒雷登对中国的深入了解给马歇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由于复杂的政治原因,最后调停失败。这时,马歇尔觉得自己已经无能为力,换一个人,也许会出现转机,而最为合适的人选当属司徒雷登。马歇尔认为“德高望重”,并且“在中国有长久经验”的司徒雷登“对于中国及其人民心理的了解,对于中国语言的运用自如,国民党和共产党对他同样的尊敬,使他具备了参与调解努力的极好条件。”于是,马歇尔致电美国政府,正式提名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我希望司徒雷登博士就任一个高级职位,这样我就能利用他对各派政府领导人的影响,所有这些人大多数他都是熟悉的。在政治谈判中他将是特别有帮助的。”尽管司徒雷登身为传教士、教育家,在外交方面似乎是个“生手”,但考虑到司徒雷登对中国和中国事务知之甚广,中国各阶层人士都能接受他,国共双方又都有他的学生担任着重要职务,美国政府还是选择了司徒雷登,并于1946年7月11日,正式任命司徒雷登为驻华大使。
中共对司徒雷登担任大使表示了欢迎。周恩来夫人邓颖超在《群众》周刊上发表谈话说:“司徒雷登先生生长在中国,对中国情形很熟悉,对我们一向有良好的友谊,而且正为中国的和平民主在努力,所以对于他的出任驻华大使很热烈的欢迎,同时也寄予很大的希望……。”国民政府中大多数人,包括蒋介石在内,也都赞同司徒雷登出任驻华大使,并对其寄予厚望。
消息在媒体公布后,燕大的师生都非常兴奋,认为司徒雷登可以发挥他的作用,为中国和平作出贡献。司徒雷登本人也是这样认为,长期以来,他一直渴望能为中国做一些更有价值的事情。应该说,做大使与司徒雷登服务中国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私下里曾对傅泾波(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顾问)说过,他不是政治家,也不为名为利,只是基于爱中国,希望中国和平昌盛,百姓少受苦难,才同意担任大使的。实际上他还有一个不好明说的原因,就是做大使更便于他为燕大寻求支持。
1946年6月,为给司徒雷登庆祝七十大寿,燕大专门成立了“司徒雷登七十大寿委员会”,由陆志韦亲任主席。生日那一天,宾客盈门,热闹非凡。前来祝寿的有国民党方面的张道藩,共产党方面的叶剑英,蒋介石还派人送来了一幅匾额为其庆生。国民政府也特地发出一道褒奖令,表彰司徒雷登对中国教育事业的伟大贡献。
7月,司徒雷登向燕大提交了辞呈,辞呈中说:“我之所以接受此项任命,完全是出于我确信此举目前最符合我为之奉献终身的燕京大学本身和其他方面利益。” 递交辞呈之后的学校茶话会上,司徒雷登又说:“今日燕京的问题,实在与中国不可分割,能出去帮忙使中国渡过今日的难关,实际上仍是为燕京工作。”燕大校务委员会没有接受他的辞呈,只是给了他一年的长假。当时司徒雷登也充满信心地认为,只需要“一年或更短的时间,就可以从我的新职务上引退,重新回到我今天离开的地方。”
1946年7月11日,70高龄的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美国驻华大使,赴南京履职,同时仍担任燕大校务长之职。同年10月,司徒雷登借参加杭州青年会复会典礼之机,祭扫了他父母之墓,杭州市参议会授予他“杭州市荣誉公民”称号,并赠送他一把象徵性的金钥匙。
司徒雷登当时充满自信,对中国的形势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他认为不能靠武力解决国共两党之间的争端,因为两党都不可能战胜对方。唯一可行的办法是建立一个联合政府。此后他以促成中国的和平为己任,致力于组建中国的联合政府,他曾这样写道:“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这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可惜事与愿违,其努力既不可能被国共双方真正接受,也从未得到美国政府的信任。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不听他的,美国政府也偏袒国民政府,他作为大使,又不得不服从美国政府的决策——他的一切努力都失败了,最后内战全面爆发。中共代表周恩来决定于11月19日返回延安。11月11日,他特意到美国驻华大使馆拜会了司徒雷登。11月16日,周恩来再次宴请司徒雷登,正式向他告别。并请中共代表团中的燕大毕业生龚澎、吴青和陈浩作陪。席间,他指着这些人对司徒雷登说:“他们是你培养的学生,你是燕大的校长,可是为我们培养了人才。”司徒雷登接口说道:“燕京的学生表现出了远非我们所能预见到的顽强性格和精神,他们充分证明了中国青年的优秀品质,中华民族的生命力和精神力量。”临别前,周恩来送给他一个明代的彩绘花瓶作为纪念。
调停失败,和平理想破灭,司徒雷登痛责自己失职,写道:“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 当时燕大校务委员会曾致电司徒雷登:“燕京需要你,最热烈地欢迎归来。”但此时的司徒雷登已经深深陷入政治漩涡之中,不能自拔。1948年,在他72岁生日前,全国各地学生纷纷罢课游行,还有38名校友联名写信给他,希望他尽快辞去大使职务,这是以前从未发生过的事情。司徒雷登回燕大仅待了三天,便匆匆返回南京。从此,他再也没有回到燕大校园。
1948年间,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1949年4月,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当时包括苏联在内的驻华使馆都随国民政府南迁到广州去了,而司徒雷登则选择留在南京静观时局变化。司徒雷登留在南京的目的很明显:国民党大势已去,正如他不久前在给马歇尔的报告中作出的预言,蒋介石“将不可避免地被抛弃”。他希望能与共产党直接接触,以便有机会讨论在新的形势下如何处理中美关系。他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问题。解决好中美关系,对世界和平将是一大贡献。在解放军打进南京的第三天,司徒雷登开始起草一份备忘录,提出关于承认中共的设想。一周后,他派人与中共联系,而中共方面负责外事工作的,正是当年司徒雷登救助过的学生黄华。黄华奉周恩来之命,多次到南京与司徒雷登晤谈,以便借助师生关系了解下一步美国政府的打算。当时毛泽东曾就如何与司徒雷登会谈以及会谈的内容提出具体的意见。后来黄华也曾回忆当年会面时的经过。司徒雷登表示,美国已经停止对蒋介石的援助,愿意与新中国建立新的关系。同时美国在中国一些地方的军队也可以作具体的调动,避免与解放军发生不必要的冲突。此后司徒雷登向黄华表示,希望能亲自去北京与周恩来面谈。周恩来通过黄华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回燕京大学一行,并表示可能一晤,毛泽东还转托时任燕京大学校长的陆志韦写信给司徒雷登,表示他可以个人身份到北平参加燕京大学校庆,并考虑安排他同有关领导人见面。获此消息,司徒雷登很是兴奋,立即向美国政府汇报情况。但就在1949年7月2日这天,他接到了国务卿艾奇逊来电,不仅不允许他去北京,还要他必须于7月25日前回国。司徒雷登虽然知道命令难违,但还是做了最后一次努力,再次提出去北平的请求。但到了7月25日,美国国务院再次电催司徒雷登,务必于8月2日前离开中国。国民党政府也希望他先到广州,再回美国,认为这将是对国民党政府精神上的支持,但司徒雷登没有这样做。根据多年后傅泾波的回忆,他曾因是否赴北平之事与司徒雷登发生过激烈的争论,但司徒雷登最终依照美国政府的指示还是未能北上。对此傅泾波甚感遗憾地说:“如果当日老人家去了北平,恐怕以后很多历史都要改写了,甚至朝鲜战争都有可能避免!”
1949年8月2日,司徒雷登不得不登上一架破旧的美国军用飞机,心情沮丧地离开他所爱的中国,离开他一生大部分事业所系之地,也离开了长眠于西子湖畔和燕园里的父母和妻子,从此再未踏上中国的土地。他乘飞机从南京直飞冲绳,并在那里发表声明,赞成中共领导的中国政府,但美国国务院未让这个声明在美国发表,还电告他不得再作声明。三天后,美国国务院发表了“白皮书”(The China White Paper)《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着重1944-1949年时期》。由于 “白皮书”公布了许多美国驻华外交人员——包括司徒雷登写给国务院的例行报告和经过“筛选”的资料,这带有很大片面性的资料给司徒雷登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使他成了美国对华政策的顶罪羊。
随后,毛泽东于1949年8月8日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文,由新华社播发,对国民党和美国当局,也对司徒雷登本人——作为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代表人物——极尽讽刺。毛泽东开言道:“美国的白皮书,选择在司徒雷登业已离开南京、快到华盛顿、但是尚未到达的日子——八月五日发表,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美国侵略政策彻底失败的象征。司徒雷登是一个在中国出生的美国人,在中国有相当广泛的社会联系,在中国办过多年的教会学校,在抗日时期坐过日本人的监狱,平素装着爱美国也爱中国,颇能迷惑一部分中国人,因此被马歇尔看中,做了驻华大使,成为马歇尔系统中的风云人物之一。在马歇尔系统看来,他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在他代表马歇尔系统的政策在中国当大使的整个时期,恰恰就是这个政策彻底地被中国人民打败了的时期,这个责任可不小。”毛泽东在文末还揶揄道:“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的美国殖民政府如鸟兽散。司徒雷登大使老爷却坐着不动,睁起眼睛看着,希望开设新店,捞一把。司徒雷登看见了什么呢?除了看见人民解放军一队一队地走过,工人、农民、学生一群一群地起来之外,他还看见了一种现象,就是中国的自由主义者或民主个人主义者也大群地和工农兵学生等人一道喊口号,讲革命。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毛泽东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中国大陆的中学语文课本里,这使得司徒雷登在中国比在美国更知名,只不过是声名狼藉罢了。长久以来,他辉煌的教育家生涯被人们所遗忘,而仅仅以“披着羊皮的狼”的虚伪形象被留在一代中国人的脑海里。
六、燕京大学的结局
司徒雷登离开燕京大学转任大使之后,陆志韦接任为燕大校长。1949 年,燕京大学根据“政府指示”进行了课程改革,增设了政治教育的课程。1951年2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批准燕大改为公立大学,并接管了她。陆志韦在庆祝会上宣布:“以后不论在名义上,在实际上,在经费来源上,教学的观点与方法上,燕京都完全而且永久的是中国人民的大学了。”随后燕大和其他前教会学校一起,掀起声讨美国文化侵略的高潮,并切断与美国的任何关系,思想改造运动亦就此开始。司徒雷登被控诉为“美国的间谍和中国人民的敌人”;赵紫宸在师生大会上痛斥司徒雷登是“美国的秘密代理人,是反苏、反共、反华的反动分子,因此是中国人民最凶恶的敌人。”但没过多久,那些批判过司徒雷登的教师也纷纷遭到批判。1952年3月,赵紫宸在全校师生大会上遭到批判,罪名是“里通外国”。陆志韦更被作为“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而遭受批斗,被控诉为“披着学者的外衣,进行亲美反共的活动,造成祖国人民不可弥补的损失。” 当时所有燕大的学者都要接受思想改造。当抗美援朝运动开始后,所有英美籍教授都离开了燕大,他们不愿意被当作“帝国主义分子”,给他们的同事和朋友带来麻烦。
1952年,几乎熔铸司徒雷登毕生心血的燕京大学被解体,分别併入了八所大学。而新北京大学的校址,便坐落在原燕京大学的校址上。至此,燕京大学不复存在。司徒雷登悲剧性的命运和燕京大学的消亡,实为那个特殊时代东西方关系的结果。
燕大虽然不复存在,但其桃李芬芳,溢美天下,遗泽后世。仅就中国外交界而言,新中国外交部的第一位女司长龚澎,中国首任驻爱尔兰大使龚普生,驻英国大使胡定一,驻意大利大使张越,驻希腊大使杨公素,常驻联合国代表凌青、副代表赖亚力,以及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南,都是燕大毕业生。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负责全程接待他的是燕大毕业生、时在中国外交部任职的韩叙,他后来成了中国驻美国大使。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时,随行人员中有四位出身于燕大。同年,黄华以外交部部长身份同美国谈判,中美正式建交。除外交界外,燕大在其他领域亦硕果累累,不再一一赘述。
七、美国晚年
司徒雷登回到美国后的生活似乎十分闲适,多有时间与家人和老朋友聚会、吃饭,但他内心里却充满了失望与惆怅。更加令他痛苦的是,在麦卡锡反共运动笼罩下的美国国务院对他下了“禁言令”,不能参加任何正式活动,同时又被麦卡锡主义者骚扰。在这一连串巨大打击下,古稀之年的司徒雷登身体迅速垮掉。1949年11月30日,司徒雷登拜访过曾在燕大任教的乔治•巴博后,在乘火车返回华盛顿途中突然中风倒下,被送进马里兰的贝塞斯达海军医院治疗。在昏迷中苏醒之后,司徒雷登第一眼看到的就是焦急守候在床边的傅泾波。在将近四个月的特护中,傅泾波每天都到医院去探望、守护,陪老人待上几个小时。出院后,傅泾波把司徒雷登接到他在华盛顿的家里,与自己和家人同住,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对待他。因中风而导致的半身不遂和失语症,使司徒雷登在轮椅和病榻上度过了最后的13个春秋。那时,司徒雷登身边没有亲人相伴,唯一的儿子也不在身边。他的生活起居完全依赖傅泾波及其家人照料。傅泾波自年少时就追随司徒雷登,从司徒雷登受洗成为基督徒,又长期生活、工作在他身边。外界一直将他视为司徒雷登的私人秘书和顾问。他和司徒雷登情同父子,一方面是由于基督之爱,另一方面是中国人知恩图报之心,同时他也是在为燕大所有的学生报答这位老人。
1952年11月28日,司徒雷登向即将离任的美国总统杜鲁门递上辞呈,提出因健康原因,希望辞去驻华大使的职务。3天后,杜鲁门在给他的回信中,对他在中国期间为增进中美关系所做的努力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司徒雷登晚年的最大也是最后一项成就是在病榻上完成了他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他在开篇第一行写道:“我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以中国为家。精神上的缕缕纽带把我和那个伟大的国家及其伟大的人民联系在一起,我不但出生在那个国家里,而且还在那里长期居住过,结识了许多朋友。我有幸在那里度过了我的童年,后来又回到那里当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当福音派神学教授和大学校长。1946年,我在意想不到的情况下,被提升为美国驻南京大使,然而,在1949年,我作为大使,最终却是很不愉快地离开了那个国家。”寥寥数语,其中国情怀跃然纸上。1954年10月15日,司徒雷登回忆录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由美国纽约兰登出版社正式出版。同年12月,中译本《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在台湾出版。1955年和1982年,香港和中国大陆也分别出版了司徒雷登回忆录的中译本,可见司徒雷登在中国的影响力之大。
1955年,司徒雷登立下遗嘱,将他的全部文件赠送给傅泾波,并要求傅泾波替他完成两个心愿:一是将当年周恩来送给他的那只明代彩绘花瓶送还给中国;而是将他的骨灰送回中国,安葬在未名湖畔他妻子的身旁。
从1960年开始,司徒雷登卧床不起,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回顾自己的一生。晚年的司徒雷登仍然坚信,“人生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荣耀上帝并且永远爱祂。”人类的生活方式越接近耶稣,世界就会变得越好;个人的命运,以及人类的命运也就越幸福。傅泾波如此描述道:“他以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和人类的仁者身份,几乎每天都在为和平、为中国的统一、为结束世界动乱等问题祈祷。”他对死亡毫无惧怕,因为他相信自己已经完成了上帝所赋予他的使命。
1962年9月18日,司徒雷登突然觉得胸间一阵隐痛,立即被送往华盛顿中心医院抢救。在那里他走完了他人生的路,安详地离开了人世,享年86岁。11月30日下午,葬礼在纽约基督教中心举行,由协和神学院院长杜森博士主持,几百名燕大校友从世界各地赶来参加了葬礼。所有人一致称赞他是一个最无私、最接近于耶稣伟大人格的人。葬礼是在管风琴演奏的中国民族乐曲《阳关三叠》中结束的。司徒雷登生前常说:“我出生在中国,也愿意死在中国。”傅泾波之子傅履仁先生这样说:“司徒雷登先生的一生都奉献给了中国的教育事业,回到中国是他最后的心愿。”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重启中美关系的大门。一年后,傅泾波应周恩来总理邀请,回到阔别24年之久的燕园,与吴文藻、冰心夫妇等燕大老友相聚。1988年5月,动过四次手术的傅泾波自感体力不支,派小女儿傅海澜专程将花瓶送还中国,陈列在南京梅园新村纪念馆内。5个月后,傅泾波在华盛顿逝世,他只完成了司徒雷登的一桩遗愿。
八、魂归故里
傅泾波之子傅履仁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华裔陆军二星准将,他和父亲两代人为司徒雷登骨灰归葬中国做了半个多世纪不懈的努力。傅泾波死后,傅履仁想尽办法,最后才将司徒雷登骨灰空运到中国。原本要葬在燕大旧址的计划已经获批,但后来又因遭到反对而搁浅。因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上层依然有人认为司徒雷登是敌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帝国主义分子,竟至联名上书反对他归葬燕园。此外,司徒雷登夫人当年逝后,被安葬在燕园的西南角,但那片地方早已被铲平,夫人的坟墓也不知去向。直到2006年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听说了司徒雷登的遗愿,并经过多方斡旋和努力,司徒雷登的骨灰才最终归葬于生于斯长于斯的杭州。此举虽然与司徒雷登的遗愿并不完全吻合,但也算是个折衷之举,在客观上也修正了司徒雷登长期以来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具有一定的驱魅效果。虽然司徒雷登的最后遗愿至今还没有完全实现,但是,从他亲手缔造了燕京大学那一刻起,他的灵魂就已经永远地留在了燕园。
2008年11月17日上午,司徒雷登的骨灰安放仪式在杭州半山安贤园举行,现场一片肃穆,音乐低迴。在美国驻华大使雷德(Clark T. Randt, Jr.)、燕京大学老校友们和杭州市民的注视下,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被轻轻安放在安贤园的文星园,四周青松苍翠,远处青山环抱。墓碑上只简单写着:“司徒雷登,1876—1962,燕京大学首任校长。” 燕京大学校友会北京校友代表国仲元把一捧洁白的百合花轻轻放在了墓碑前:“老校长,您安息吧。” 杭州校友姚林杰感叹说:“司徒雷登先生总说西湖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这里就是他的故乡。今天,他总算回家了。”
司徒雷登在杭州的出生地——耶稣堂弄的故居也已于2002年得以恢复并修缮,作为文物得到保护。又于2005年6月辟为“司徒雷登纪念馆”对外开放。当年国民政府授予司徒雷登的“杭州市荣誉市民证书”,并那把象征荣誉市民的金钥匙,如今也静静地陈列于馆内。
历史学家林孟熹如此评论司徒雷登说:“整个20世纪大概没有一个美国人像司徒雷登博士那样,曾长期而全面地卷入到中国的政治、文化、教育各个领域,并且产生过难以估量的影响。”诚然如此,过去因着许多复杂的历史和政治原因,中国人,特别是生长于中国大陆的中国人对司徒雷登的评价有失公允。他一生绝大部分时间以中国为家,为中国效力,对中国的贡献远超过许多中国人。美国人可以忘记他,但中国人不应该忘记他,北京大学更应该感念他。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每个人都有其局限性,但纵观司徒雷登的一生,相信每个人自会得出一个公允的结论:他是一个伟大在传教士、教育家、学者、仁者和爱国者——尤爱中国;他对中国的教育事业,以及对中国革命贡献甚巨,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中美关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资料来源
- Stuart, John Leighton,The Forgotten Ambassador, The Report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1946-1949. Westview Press, 1981.
- Yu-ming Shaw, An American Missionary in China: John Leighton Stuart and Chinese-American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2.
- Philip West,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 司徒雷登著,常江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海南出版社,2010年7月。
- 李跃森著,《司徒雷登传》,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1月。
- 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载《毛泽东选集》四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第2版,第1491页。
- 特约记者吕贝卡,“消失的燕京大学,被遗忘的司徒雷登”,《时代周报》, 2013年9月19日。
- “司徒雷登魂归杭州,骨灰葬于半山安贤园”,网易新闻,2008年11月18 日。
- “司徒雷登归葬中国”,金羊网,2014年4月30日。
- “魂归故里:司徒雷登骨灰安葬杭州的前前后后”,凤凰资讯,2014年4月30日。
- “美国前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骨灰安放杭州”,北方网,2014年4月30日。
关于作者
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