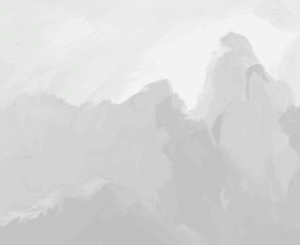W.Limpricht在1912年说到:“他的动物学藏品种类之多,前无古人,更不用说超越了。至于他考察过的地区的地质学和植物学,最大的进步都要归功于他。”另一个德国人Hartlaub也在1876年评价说“他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探险家和博物学家之一”。
谭卫道于1826年9月7日出生在法国巴约讷(Bayonne)附近的埃斯佩莱特村(Espelette)。他的父亲是当时的市长和医生,对大自然有着强烈的热爱和好奇心,谭卫道继承了这些特质。他除了是法国遣使会传教士外,也是一位杰出的地质学家、植物学家、鸟类学家、昆虫学家、哺乳动物学家。在他那个时代,教会的职业生涯和对自然科学的追求并不冲突,而在这些不同的研究领域,他都有卓越的成就。他在巴约讷神学院学习两年后,于1848年前往巴黎,在遣使会见习,并被祝圣为神父。他于1850年11月宣誓时,就想着去远方传教,但他先被派往意大利热那亚附近的萨沃纳的拉扎里斯特学院(Lazaristes de Savone)教授自然科学,他利用这十年来完备其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
1852年,谭卫道向教会提出要到中国传教的申请,1862年他被派往中国北京。当此消息传到法国科学界时,许多科学家要求允许他为巴黎自然史博物馆收集标本。因此,1862 年,谭卫道带着修改后的命令被派往中国。
当时,世人对中国的动物和植物所知甚少,谭卫道可说是来到一个科学的宝地。但另一方面,当时的清朝正处于太平天国之乱、捻乱和同治陕甘回乱的时期,软弱腐败的清中央政权也遭受了法英殖民军队的打击。清朝在英法军队面前惨败后,才开放让西教士传福音的权利,但同时也导致清官员们对传教组织产生了帝国主义的敌意,视之为外国试图觊觎中国领土与资源的手段。但谭卫道对动物学和植物学充满热情,大部分时间都独自一人面对大清帝国的数千种自然和人类危险(愚民政策和仇外心理)。
1862年2月20日,谭卫道从土伦出发,经过大约五个月的旅程,绕过好望角到达中国。“在学习这个国家的语言的同时,并在神职人员的工作中进行合作,我开始探索首都的周边地区”,他写道。1862年到1866年,他在北京附近进行了第一次探索。1863年夏天,他先探索了北京以西的山区;次年5月,他又探索了承德市附近的热河行宫。这时谭卫道发现了麋鹿 (Cervus comeloides),后称之“大卫神父的鹿”(Elaphurus davidianus)。这种鹿因具有鹿角、骆驼颈、牛足、驴尾而得名“四不像”。这种在野外几乎灭绝的动物由士兵看守在皇家猎苑。谭卫道把活的麋鹿引回了欧洲,并建立了几个繁殖群。1895年,皇家猎苑围墙被洪水冲垮,许多鹿被饥饿的农民吃掉。其余的在1900年义和团运动期间被消灭。在20世纪80年代,几十头鹿从欧洲引回到中国,并被放到当年的猎苑。此后又进行了几次移植,如今在中国的各个自然保护区中已有数千头麋鹿。
谭卫道收集到的标本送到巴黎,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在博物馆的教授请求下,谭卫道获得了特别的许可,免除所有的传教工作,让他专门从事自然探索。同时,法国内政部授予他官方使命的称号,并提供必要的费用。于是在公共资助下,谭卫道到中国鲜为人知的地区进行了三次大探险(1866,1868-1870,1872-1874),成功获得当时未知的动物和植物的许多标本,并且他的全面收藏对系统动物学的发展,以及对动物地理学的推进做出很大贡献,获得了科学界的普遍认同。
1866年3月至10月,谭卫道前往蒙古南部进行了为期七个月的探索:
- 当时,欧洲人还完全不了解蒙古,甚至北京的学者对蒙古也知之甚少,以至于找不到任何地图,只能根据喇嘛提供的信息手绘草图。3月13日,谭卫道偕一支探险队离开北京,前往探索蒙古地区。由于气候非常恶劣、缺乏水和食物,以及路上强盗和军队造成的不安全,这段旅程非常艰难,需要坚强的体魄才能克服环境的考验。
- 每天,他都对所观察到的一切做出大量的笔记:土壤的性质、粮食作物、动植物、人们的习俗和宗教等等。他这支探险队的大本营位于呼和浩特市和包头市之间的萨拉齐镇。他们收集了176种鸟类、59种哺乳动物、1500个植物标本和680个昆虫标本。
- 在这次探险中,谭卫道将第一批“沙鼠”从蒙古送到巴黎。后来,这20对繁殖的沙鼠成为今天所有宠物沙鼠的父母。
- 谭卫道于1866年10月返回北京,直到1868年5月,他一直忙于他计划中的大学和自然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后来的北京西什库天主堂,又称北堂的百鸟堂博物馆)。后来,谭卫道曾在西什库教堂设立标本陈列室,据樊国梁主教(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1837-1905)的《燕京开教略》所记:谭卫道“抵华后,遍游名山大川,收聚各种花卉鸟兽等物,以备格致,即于北堂创设博物馆一所,内储奇禽计八百余种,虫豸蛱蝶,计三千余种,异兽若干种,植物金石之类,不计其数。”当时吸引了许多王公贵族前来参观,慈禧太后也曾微服参访过。
此外,基督教《教会新报》(Church News)、《万国公报》(The Globe Magazine) 的主办人、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林乐知(Andrew Young John William Allen)也曾于1875 年在《万国公报》第362 期刊载了一篇“书申报创设博物院后”,提到自己曾到北京这座博物馆参观的经验,其云:“搜罗直隶、蒙古、满州,以及山西、陕西并泰西各处奇禽异兽,大而狮子、小而燕雀,无一不备,即螳螂、蚱蜢等物亦列其中。死者如生、枯者转荣,居然有活泼泼之机焉。”
1868年5月26日到1870年6月24日,考察中国中部和西藏东部(四川):
- 谭卫道从其他传教士那里得知,在中国西部和西藏有一些高山覆盖着、保存完好的原始森林,他就沿着长江逆流而上,却因为当时的河水汹涌被困在九江。他在那里待了四个月,探索周边地区,并两次登上庐山。在这次停留期间,他收藏了十种哺乳动物、植物约有200种、三十种鸟类、50 或60 种鱼类或爬行动物,鞘翅目有335种,半翅目有100种——总共有630种昆虫。
- 1868 年 10 月 13 日,河流可以通航了,他出发继续探险。急流的通过不能用桨,必须由几十个人拖着长绳子拉着船逆流而上。不只旅途艰苦,他还必须面对人们的敌意,把他当作间谍,侮辱他,有好几次,他怀疑有人在他的茶里下毒。
- 12月17日,他抵达重庆。他将步行或乘坐轿子到达成都以西约250公里处的穆坪镇外方传教学院(现四川省雅安市宝兴县盐井乡的邓池沟圣母领报堂)[1]。谭卫道将这里作为他的基地,他说此地是他的“应许之地”。他在该地区进行了为期9个月的探索。
- 对谭卫道来说,这些山脉与大清王朝的军队、和统治该地区的土豪之间的摩擦一样危险。有一次,当他和他的向导试图抓住雪中矮小的树木越过陡峭的山脊时,冰雨开始落下时,他和他的向导迷路了。后来他们听到了远处的声音,并被山民救了出来。
- 标本的准备和制作困难巨大,难以找到保存兽皮所需的明矾,没有橱柜和箱子来保护遗骸免受虫和细菌的侵害,过高的温度与过量的降雨使得空气中的水气处于饱和状态。此外,因百姓不擅使用木板、钉子,谭卫道必须自己制做木箱来包装。还有,他因长期肠道剧痛,无法正常排尿,但也无法得到任何医疗帮助,他只能自行吃草药,别无他法。
- 谭卫道的成名就是由于此次探险的一些伟大的发现,例如大猫熊、金丝猴和珙桐。
1869年3月11日,他受邀与猎人一起喝茶,他看到了一个相当大的兽皮:白色和黑色的熊。3月23日,猎人“他们以很高的价格卖给我的小白熊,除了四肢、耳朵和眼睛周围是深黑色外,它全身都是白色的。”“一个月后,成年熊来了,我可以看到这种动物的颜色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变……。它生活在最人迹罕至的山区,以植物为食,尤其是竹根”。这就是大猫熊。
- 谭卫道还发现金丝猴,因为它们鼻孔朝天,谭卫道将它们命名为“仰鼻金丝猴”(Rhinopithecus Roxellana),这个名字直到今天还在沿用。
- 谭卫道还发现了一种孑遗植物—珙桐。珙桐像大猫熊一样躲过了第四纪冰川期,花开时节,成双成对的“花瓣”像是满树飞舞的鸽子,因此谭卫道称它为“中国鸽子树”。1904年珙桐被引入欧洲和北美洲,成为有名的观赏树。
- 他还区分了13种不同的杜鹃花。
- 谭卫道从四川向巴黎的博物馆送了676件植物、441件鸟类、145件哺乳动物标本。
- 谭卫道于1869年11月22日离开了“曼兹人的国家,在遭受了比这里所说的更多的疲劳、痛苦、贫困和疾病之后”(一场当地人称之为“骨斑疹伤寒”让他发烧许久,另一场发烧让他的脚肿胀,在床上躺了12天)。同年12月至次年3月,他绕道青海高原,发现了中国大鲵(Andrias davidianus,原名Sieboldia davidii)。
- 1870年6月24日,反基督教和反法骚乱发生三天后,他死里逃生,乘船离开上海。身为一个有着坚定宗教信念的欧洲人,他无法理解这些屠杀,内心深受创伤。
- 1870年8月底,他抵达法国马赛,然后前往巴黎,忙于抄写考察笔记并撰写探险之旅回忆录。恢复健康后,他计划深入探索中国的中部地区。
1872年10月至1874年4月,谭卫道从秦岭到江西的探索:
- 1872年3月,谭卫道到浙江进行了一次小规模的探索。
- 1872年10月,谭卫道到西安以南的秦岭探险。当时那是一个仍然荒凉的山地屏障,是黄河流域(及其支流渭河)和南方长江流域(及其支流汉江)之间的分水岭,它也分隔北部温带气候区和南部亚热带气候区,这位置使得植被和动物特别丰富。
- 1872年11月,他停留在一个相当偏僻的小村庄殷家坡。他说到:“我们很不高兴地看到这些原始森林的破坏速度如此之快,在中国各地只剩下残片,而且永远不会再被取代。随着大树的消失,大量只能在阴凉处繁殖的灌木和其他植物也随之消失,还有许多大小的动物都需要森林来生存和延续自己的物种。不幸的是,中国人在这里做的事情,其他人在其他地方也在做。令人遗憾的是,人类的教育没有及时发展到足够的程度,无法及时拯救如此多的生物免遭不可挽回的毁灭,造物主将这么多有组织的生物安置在我们的地球上,与人类共同生活,不仅是为了点缀这个世界,而是在整体经济中发挥有益且必要的作用。自私和盲目地专注在物质利益,让我们懂得欣赏的人看来,是将这个奇妙的宇宙简化为一个平庸的农场。……与我们共同生活的成百成千种动植物,它们拥有生存的权利,而我们却残酷地的消灭它们,让它们无法生存。”150年前就有如此之洞见,令人敬佩!
- 1873年1月初,他再次踏上秦岭直到4月,继续收集动植物,并对当地的地质、鸟类的迁徙和人们的风俗习惯做出非常详细的描述。接着他进入汉江流域,到达汉口,入长江。但在经过急流时,超载的船撞到了岩石,估计一半的植物收藏因而损失了。
- 恢复体力后,1873年5月22日,他往东南方向走去,经南昌,他定居在江西抚州,在不卫生和酷热的折磨下,谭卫道和他的中国助手感染了疟疾,健康状况迅速恶化,整个夏天他都只能躺在床上或房间里,但仍然努力研究所有被带到他面前的标本。
- 九月底,当他感觉好一点时,他前往福建山区,他以超人的努力为代价,在体力耗尽的情况下到达了某个小村。但他的健康状况进一步恶化,以至于人们为他举行了最后的仪式,还好他坚强的体质再次拯救了他。
- 他如此写道:“归根结底,尽管遭受了种种苦难,我发现自己对江西东部和福建山区的收藏很满意。它们装满了两个大板条箱、另外三个小板条箱和九个不同尺寸的箱子。光是这里采购的大大小小的哺乳动物就有35到40种不同的物种,其中有几种是新的,鸟类也是新种的,爬行动物、昆虫等也是如此……。”
在三次伟大的远征之后,谭卫道回到了法国。他在巴黎过着平静的日子,整理了所有从中国带回来的科学笔记,并为神学院的学生讲课。他还承担了他一直非常关心的任务:建立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这是他继意大利萨沃纳和北京北堂之后,所创建的第三个博物馆。
1875年,他与阿歇特(Hachette)一起出版了两卷大卷本《中华帝国第三次探险日记》。两年后,他出版了一部关于中国鸟类的杰作《中国的鸟类》,包括有807种。
1888年4月,谭卫道在巴黎举行的天主教国际科学大会的致辞里面总结了他的研究:
- 他在中国发现了200多个种类的动物,其中63种当时不为动物学家所知,包括北京的麋鹿、大猫熊以及金丝猴和藏猕猴、蝙蝠和众多啮齿动物。生活在中国的四种羚羊中他发现了三种。
- 他并且发现了807种鸟,其中65种以前从未被描述过。
- 他大量的收藏爬行动物、无尾两栖动物和鱼类,并把它们送给物种学家进一步研究。
- 他还大量的收集飞蛾和昆虫标本,大多数在当时都不为人所知。
- 他对植物学的贡献:在他收集的杜鹃花之中有不少于五十二个新种类,在他收集的报春花之中大约四十种是当时未知的。大叶醉鱼草的学名Buddleja davidii就是纪念他发现此品种。此外还有青榨槭(Acer davidii)、刺榆(Hemiptelea davidii)、西北蔷薇(Rosa davidii)、白刺花(Sophora davidii)以及珙桐(Davidia involucrata)。
但他在大会上因捍卫达尔文进化论而受到广泛的嘘声。
谭卫道运送到巴黎自然史博物馆(National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 France)的标本数量相当可观:有2919种植物标本;9569种昆虫、蛛形纲动物和甲壳类动物标本;1332种鸟类和595种哺乳动物标本。其中大约70个植物物种的科学鉴定以他的名字命名。
1900年11月10日,谭卫道在巴黎去世,享年74岁。
脚注
[1] 1830年左右,巴黎外方传教会在穆坪鎭邓池沟地开设领报神学院(Collège de l'Annonciation),即现在的邓池沟圣母领报堂。这座教堂的名气得益于大猫熊的发现者—法国遣使会传教士谭卫道。他于1869年到达穆坪鎭,研究当地动植物。当时在领报神学院的传教士大多都是自然科学家,包括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他们常与巴黎的各种科学院联络、谈论在四川的新发现。
资料来源
- 戴丽娟,“公共博物馆在中国的第一百年(1829-1929)”,台湾:《人文与社会科学简介》24卷1期,2022年6月8日。
- 若望,“传教士谭卫道传:国宝大猫熊的发现者”,《基督时报》,2019年6月4日。
- “发现麋鹿、金丝猴和大猫熊的人”,《搜狐》,2017年05月03日。https://www.panda.fr/sur-les-traces-du-pere-armand-david-dans-la-principaute-de-moupin.html
- https://fr.wikipedia.org/wiki/Armand_David
- Christopher Howse,《天主教先驱报》,2013年9月8日。
- Le père David[PDF], Les Missionnaires Français chasseurs de plantes, sur www.rhododendron.fr
关于作者
作者系美国加州基督工人神学院硕士班学生,在李亚丁博士指导下撰写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