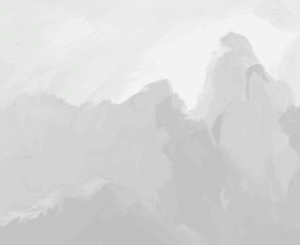一、早期背景
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于1829年12月5日出生于英国苏格兰法勒科尔克城(Falkirk),是七个兄弟中的长子。年轻时进入苏格兰格拉斯哥大学读书,获法学和神学博士学位后,于1855年被伦敦宣道会按立为牧师,并接受伦敦会之差派,偕夫人伊莉莎白一道来华宣教,于1855年9月24日抵达山东烟台,成为最早到达烟台的基督教传教士。
二、在华岁月
韦廉臣和夫人在烟台以西的通伸村购置了13亩土地,建造了一座英式教堂和住所,除开荒布道外,还在烟台市和通伸村各建一所医院,并开办学校,成为烟台现代医疗与文化事业的开端。韦廉臣常常骑马到烟台附近城乡传道,因其满口胡须,人皆呼他为“韦大胡子”。韦廉臣夫人在烟台特为穷苦女孩子开办了一所女校,招女生30余人,由教会提供食宿。韦夫人待这些女孩爱如己出,她为人又极和善,每遇穷人,必行周济;每遇孤儿寡妇,必施以援手。故教会教友及其学生,皆视她如慈母一般。
韦廉臣和夫人只生有一个女儿,名叫Margaret Williamson,生于1861年他们返英治病期间。由于长年劳累,韦廉臣健康受到损害,于1857年底不得不返回英国治病,直到1863年才再次来华,并一直在烟台传道,因此人们提到他时,常称他为“烟台韦廉臣”。此后6年之久,他作为苏格兰圣经会(National Bible Society of Scotland)的代表,除了在山东境内,还先后到华北、东北、外蒙古等地旅行、销售圣经,散发福音书册,并考察当地风土人情。1866年,韦廉臣从烟台乘船出发,在东北牛庄(今辽宁营口)登陆,再一路北上,先后到达双城(今黑龙江双城市)、阿什河(今阿城市)、三姓(今依兰县)等地宣教。韦廉臣到达黑龙江的具体时间是1868年5月,这是有史以来基督教进入黑龙江的最早记录。1869年8月,他的弟弟,伦敦会传教士James Williamson在天津附近被杀。同年韦廉臣再次返回英国休假,期间他写作并出版了其着著作《华北、满洲及东蒙旅行记》,也因此于1871年被格拉斯哥大学授与荣誉法学博士学位。
1871年底,韦廉臣重返烟台。1876年《烟台条约》签订后,韦廉臣以苏格兰圣经会传教士身份,到济南销售圣书,因此成为第一位进入济南的基督教传教士。
三、韦廉臣与墨海书馆
墨海书馆(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Press)是由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于1843年在上海创办的,是中国第一个编译出版机构。该馆最初任务是为教会出版圣经和福音书册;自1850年起,墨海书馆开始翻译、出版和印刷西方的科技书籍,范围涉及数学、几何、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动植物等各个领域,声誉与影响日增,有些书籍甚至被引入日本,对日本的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墨海书馆从1843年创办到1863年停办,历20年之久。韦廉臣于1856-57年间参加墨海书馆的译述工作,时间大约二年左右。期间他与中国著名学者李善兰合译了英国植物学家林德利(John Lindly)所著的《植物学基础》(Elements of Botany),以《植物学》为中文书名,于1859年由墨海书馆出版。此书是近代中国最早的植物学译著,比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植物学知识,对中国近代植物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许多专用名词,如“植物学”、“科”等词由此确立。《植物学》出版后,受到学术界的好评,被认为是了解西方植物学最好的入门书。中国植物学界认为此书面世之后,近代西方的普通生物学才算传入中国。很多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都读过这本书。梁启超说:“动、植物学,推其本原可以考种类变之迹,究其致用,可以为农学畜牧之资,乃格致中最切近有用者也。《植物学》、《植物图说》皆其精。”《植物学》出版后不久就被传入日本,1875年,日本学者根据中译本,转译为日文出版,随即被日本植物界视为近代植物学史上的重要文献。
四、韦廉臣与《六合丛谈》
《六合丛谈》月刊是由墨海书馆发行的综合性杂志,于1857年1月26日创刊,由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担任主编。其内容包括科学、文学、新闻、宗教等大量科学知识,成为近代上海的第一份综合性杂志。韦廉臣是《六合丛谈》的撰稿人之一,曾撰写多篇有关科学与基督教信仰的文章,因为韦廉臣来华后很快察觉到,单纯直接地传播基督教信仰很难得到中国人的认可与接受,所以他藉传播科学的同时也传播基督福音。比如在其连载于《六合丛谈》上的《真道实证》里,韦廉臣介绍了化学元素的概念及其组成定律,论述了有机物的结构。当时他所介绍的化学元素已达64种,意在说明上帝创造万物的奇妙,从而使中国人相信上帝的存在。
韦廉臣不仅介绍了近代科学知识,还向中国人宣传近代科学的重要意义。他写的《格物穷理论》就是一篇专门论述近代科学的重要性的文章。他认为,科学技术关系到国家的富强,指出:“国之强盛由于民,民之强盛由于心,心之强盛由于格物穷理……。精天文则能航海通商,察风理能避飓,明重学则能造一切奇器,知电气则万里之外,言信顷刻可通,故曰心之强由于格物穷理。”这里的“格物穷理”即指近代意义上的科学研究。韦廉臣在该文中还详细介绍了西方社会生活在科学技术影响下发生的各种改变,以及近代科学技术在海陆、交通、农业、工业、通讯等方面的应用,而当时中国对这些却一无所知,这些使中国人了解到西方的船坚砲利是以近代科学知识为基础的。他认为要使中国富强起来,就应当致力于“格致之学”。韦廉臣所介绍的新观念有助于中国人认识客观世界,并改造世界的重要力量。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些新思想的启发之下,提出“采西学”、“制洋器”等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主张,进而对中国社会上层实权派人物,如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六合丛谈》因此成为晚清自强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五、韦廉臣与益智书会
1877年5月,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举行了自基督教入华70年来的第一次宣教大会,在这次大会上,传教士对教会办学模式进行了热烈的反思和探讨,韦廉臣提议在上海成立一个常设机构,专门处理教科书编写与出版事宜。最后大会通过了决议,同意韦廉臣的提议,建立了School and Textbook Series Committee(直译为“学校教科书委员会”),其中文名称定为“益智书会”。该书会委员包括韦廉臣、丁韪良(W. A. P. Martin)、狄考文(Calvin W. Mateer)和傅兰雅(John Fryer)等人。在益智书会的初旨中,基督信仰的地位是高于科学的,传播科学是为了传福音,韦廉臣尤重这点。他曾明确指出:“科学与上帝分离,将是中国的大灾难”。如果实行分离,学生们“既不信仰上帝,又不相信圣贤和祖宗,”那将会使中国陷入崩溃,只有把基督教信仰和科学结合起来,才能够拯救中国。
益智书会后来在编译教科书的同时,也在统一科技术语方面做出很大的努力,包括数学术语、天文术语、机械术语、各恆星的名称,以及科学地理和历史的术语的统一;也包括圣经新旧约全书文理译本所用的人名地名,以及道教和佛教的名词和成语等。虽然所取得的成就有限,但毕竟为统一术语译名的工作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益智书会所出版的各种教科书和科技译著,对晚清社会和教育界的影响相当广泛,这些书籍为中国人培养了自编教科书的能力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中国人自编新式教科书比益智书会晚了20多年,而且在许多方面是从益智书会中吸取了有益的成分。
自1877年益智书会在上海成立后,韦廉臣一直在其中担任重要职务。此间,他于1884年在英国创立了“中华圣教书会”(Book and Tract Society for China),后于1887年在上海改名为“广学会”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直到他去世的三年,一直执掌着广学会,但他并没有卸任益智书会的职务。在1890年举行的全国基督教宣教大会上,决议将“益智书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将其影响扩大到教会之外,以囊括整个“中华教育”。韦廉臣提出以基督教信仰来吸引并塑造中国青年,他说:“中国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未来的中国就在于他们如何把它建立。因此,我们的努力应当大部分着眼于他们。青年是我们的希望,如果我们失去他们,我们就失去一切。……如果我们忽略或是不把上帝的存在和属性所显示的神奇事实传授给他们,感动他们的良知,淨化和提高他们的心灵,我们将失去一切。”
六、韦廉臣与广学会
在晚清中国,出版西书影响最大的有三家:一是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主持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二是由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主持的京师同文馆;第三家就是广学会。前两家虽然由传教士主持,但都是由中国政界和学界中有识之士为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知识以求自强而建立的。而广学会则完全是由传教士所办的出版机构,而且其规模和出版书籍的数量都远远超过前两家。
1883年,韦廉臣因为健康原因回到苏格兰。1884年他在英国组织成立了“中华圣教书会”,后称为“同文书会”(Society for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直译为“在中国人当中传播基督教及一般知识的会社”),又于1887年11月更名为“广学会”。韦廉臣用他在英国所募捐来的钱款购置印刷机器,在上海设厂印刷中文书籍。他联络了海关总税务司赫德(Robert Hart)、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和慕维廉(William Muirhead)等人,于1887年11月在上海创立了广学会,此时离韦廉臣去世只有三年时间。会员主要是在华西方传教士,会长由赫德担任,韦廉臣为协理兼任书记,负责日常工作。事实上,他是广学会的实际决策者。
关于广学会建立的宗旨,韦廉臣在他起草的《同文书会发起书》中指出:“本会的目的归纳起来可有两条:一为供应比较高档的书籍给中国更有才智的阶层阅读;二为供应附有彩色图片的书籍给中国人家庭阅读”。由此可见,韦廉臣创立广学会,旨在出版适合中国文人学士和官员阅读的高档书籍,再藉由他们影响其家人和朋友,并最终影响到中国人民大众,以达到中国接受基督教信仰和西方科学文化的目的。
广学会成立后,韦廉臣在上海设立书刊发行中心,一方面通过各种关系和渠道,向中央和地方政府官员赠书;另一方面在中国各省会和主要城市设立代销点售书,并且每逢各地举行乡试、省试、会试等科举考试时,派人到考场外面送书;而且还不时以举办有奖征文等手段来吸引士大夫阶层。
韦廉臣执掌广学会直到1890年8月因病去世,其继任者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将广学会进一步推向鼎盛时期。
七、韦廉臣与《万国公报》
《万国公报》的前身是创办于1868年9月的《教会新报》,主编是林乐知,初衷是为了联络教会和造就信徒,内容多注重在基督福音方面。从第三年开始,教会和教义内容大为减少,而世俗消息、科学技术方面的内容则明显上升。
1874年9月《教会新报》改名为《万国公报》(Globe Magazine);到1883年7月,《万国公报》曾一度停刊。广学会创立之始,韦廉臣就想要创办一份期刊,故于1889年2月,他和林乐知等人决定将《万国公报》复刊,仍由林乐知担任主编,此后《万国公报》就成为广学会的机关报,成为其喉舌和舆论阵地了。除主编林乐知外,韦廉臣、慕维廉、艾约瑟和花之安(Ernst Faber)等传教士都分任有关职位,将《万国公报》办成一份向近代中国传播西方学术和西方政治思想的重要杂志。
韦廉臣一生著述颇丰,他的大部分作品都发表在《万国公报》上,停刊前复刊后都有。即使在他去世以后,其很多遗稿还继续被刊载在《万国公报》上。
韦廉臣在《万国公报》上对中国的教育非常关注,在其《治国要务论》一文中,他强调女子接受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他还特别对日本的教育制度进行了介绍。日本过去在文化上一直受中国文化的深刻影响,它的教育制度也是基本上因袭中国的。到了19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明治政府在文化教育上锐意改革,在“文明开化”的口号下,“求知识于世界”,废除以传统儒学为中心的封建教育,建立起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推行全民普及教育。韦廉臣曾两次去过日本,亲眼目睹了日本教育体制的转变。回到中国后,记下了日本的见闻,集成为《东洋载笔》一书,发表于1874年《教会新报》上。这篇文章可能是近代中国最早描写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教育改革的文章。可惜被介绍到中国后,根本没有引起国人的注意。
八、韦廉臣的《格物探原》
历数韦廉臣发表在《万国公报》上的文章,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格物探原》,该著作连载于1874-1876年的《教会新报》和《万国公报》上,最能代表韦廉臣传播科学与传播基督教信仰并重这一宗旨。1876年上海美华书局出版了《格物探原》单行本;1889年,墨海书馆又出版了六卷本的《格物探原》。该书发行量大而且广,不仅在近代中国,而且在日本也受到相当的重视,曾在日本天皇特许下,一版再版此书。
《格物探原》主要介绍了天文、地理、地质、生物和人体构造等多方面的知识,并附有大量精美的图片。韦廉臣将基督教神学与信仰融汇在科学知识中,以自然科学来说明上帝的全能与全智,以及基督教的优越性,整本书都贯穿着对上帝智慧的无限崇敬。他介绍科学知识就是为了向读者展示上帝创造的精妙的万物、上帝的仁爱之心,以及上帝的智慧与伟大。他把《格物探原》中所介绍的科学知识几乎都最终归因于上帝的安排,书中不少篇幅是直接的弘扬上帝,传扬福音,规劝人们信奉上帝,并以圣经的标准劝人为善。总体来说,《格物探原》一书以基督信仰为体,以科学知识为用。格物,即是自然科学;探原,则将一切归于上帝。该书独特之处还在于,世俗之人可以将它作为科学书籍来阅读,而基督徒也可以将它作为宗教书籍来阅读。
九、病殁于烟台
韦廉臣最后一次从英国回到上海是在1886年,不久夫人去世。1890年5月7-20日,韦廉臣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第二次在华传教士大会。仅三个多月后,即于1890年8月28日,韦廉臣病殁于山东烟台,享年61岁,与妻子合葬于烟台毓璜顶西侨公墓。其墓碑由红色花岗岩凿成,长约一米半,宽约0.4米,上面镌刻着:
此碑铭志
韦廉臣
1829年12月5日生于法勒科尔克
1890年8月28日卒于烟台
苏格兰联合长老教会牧师
格拉斯哥大学法学博士
自1855年起,向中国人传扬福音的传教士
归属
This article is reprinted from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Macmillan Reference USA, copyright (c) 1998 Gerald H. Anderson, by permission of The Gale Group;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Grand Rapids, Michigan. All rights reserved.
资料来源
- Broomhall, Alfred,Hudson Taylor and China's Open Century: Survivors' Pact. London: Hodder and Stoughton,1984.
- 田勇硕士论文,“韦廉臣在华的西学传播与传教”,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
- 熊月之著,《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 汪子春,“我国传播近代植物学知识的第一部译著《植物学》”,《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年第3卷第1期。
- 王扬宗,“《六合丛谈》中的科学知识及其在清末的影响”,《中国科技史料》,1999年第3期。
- 王琳著,《西学与变法——<万国公报>研究》,济南:齐鲁书社,2004年。
- 王立新著,《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
- 梁元生著,《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
- 孙邦华,“《万国公报》对西方近代教育制度的植入”,北京大学学报,2002年第3期。 刘广定,“《格物探原》与韦廉臣的中文著作”,《中国近代科技史论集》,台北:中央研究所,1991年。
关于作者
作为世华中国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李亚丁博士现担任《华人基督教史人物辞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执行主任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