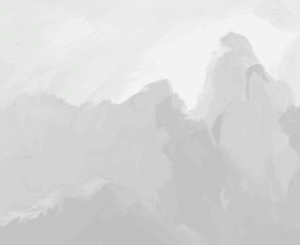希祝虔这个名字是其英文名字Eugene Hill按照粤语译音而来。希祝虔于1910年出生于德州诺克斯城(Knox City, Texas)的一个敬虔爱主的家庭。出生后没多久,父亲希班顿(Benton Hill)和母亲奥诗尼尔(Othniel)就带小祝虔搬到俄克拉荷马州罗屯(Lawton, Oklahoma)的一个庄园。在祝虔之后,家中又添了六个弟弟。就在他即将小学毕业时,母亲因病而辞世。有一天,一位牧师来到罗屯,在父亲班顿的帮助下,建立了教会。当牧师在主日证道后向会众发出呼召时,祝虔立即走向圣台前决志信主,成为一个基督徒。
丧失爱妻的希班顿决定卖掉令人伤感的庄园,搬到靠近自己家人的地方居住。但当他带着所得的大笔现金,骑马返家的路上,不幸遭遇歹徒袭击身亡。父母双亡后,13岁的希祝虔到杜兰城与祖母同住,并得以进入当地一所中学就读。他不愿向祖母要钱支付学费和生活费,故每天早上五点到一间食品市场打工。身为长子的希祝虔还独自担负起照顾弟弟们的责任,暑假时到德州的油田去打工,虽然油田的工作非常危险,但是油井的工作待遇优渥。每天中午休息的时间,他自己就找个角落读圣经。在油田的工人,由于离家在外,再加上高危险性的工作,心灵多孤寂忧虑,但他们看到祝虔的脸上,却时常流露出平安与喜乐。终于有一天,有几个人来到祝虔读经的角落,请求祝虔带领他们查经、祷告。应油田工人的请求,祝虔改变了自己的计划。暑假结束后,他留在油田中继续带领查经祷告和聚会,同时亦应邀到榆景镇(Elmview, Texas)的教堂去牧会,那时他才17岁。
19岁那年,希祝虔辞去德州油田和榆景镇教牧的工作,回到俄克拉荷马的杜兰城,一边打工,一边在东南师范学院读书,同时还在一所乡村教堂讲道。两年半以后,他转到了俄克拉荷马浸信会大学就读,在那里认识他未来的妻子露易丝(Louise)。希祝虔在俄克拉荷马州大毕业后,又到肯塔基州路易维尔城的神学院进修。露易丝则照着原来的计划要在三年内拿到学位。就在露易丝毕业那年,即1934年9月6日,他们在露易丝父母――海瑞克夫妇的家中结婚了。
婚后,年轻的希氏夫妇住在肯塔基的马窟镇(Horse Cave, Kentucky),因为当时希祝虔仍在神学院深造,同时在马窟镇牧养教会。有一天,露易丝接到“海外宣道部”麦德理先生(Dr. C. E. Mddry)的电话,约他们马上赶往维吉尼亚州的列治文(Richmond, Virginia),到美南浸信会的总部面谈。原来是浸信会在广州的“两广神道学院”(Graves Theological Seminary)校长梁根(Theron Rankin)博士即将离职,需要一位校长人选来接替他。面谈之后,总会认定希氏夫妇是最理想的人选。于是,他们立即辞别了马窟镇的教会,匆匆与亲人道别,于1935年12月13日搭乘“克里夫兰总统号”轮船前往中国。那年,希祝虔才25岁。
希祝虔和露易丝到达广州的第一件事便是学习广东话(粤语),这是一个非常不易学习的语言。在纪好弼医生(Dr. Rosewell H. Graves)的鼓励下,希祝虔在一年内即打下良好的粤语基础。当语言学习告一段落后,希祝虔一面在两广神道学院教书,一面在东山浸信会堂负责讲道和主日学的工作。他也经常搭乘公车,到附近的村镇去讲道,生活非常忙碌。有一次,希氏夫妇到一个小岛上度周末时,希祝虔不幸染上恶性疟疾,当即被送到香港一家英属医院急救。虽然他昏迷多日,但最终总算被抢救过来。
1936年10月,希氏夫妇第一个女儿诞生了。但这个小生命来到世上只几个小时,便悄悄地走了。他们心中哀痛万分,把她小小的身躯埋葬在附近一个宣教士与家属的墓地里。1937年7月,但他们第二个女儿降临时,正值“卢沟桥事变”之后。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夜晚,这个小生命也未能留住。他们怀着悲伤心将次女埋葬在她姐姐的旁边。
抗日战争爆发后,在1937年7月底,北京和天津便告沦陷。由于广州是中国国军的军事基地,因此遭到日军飞机猛烈的轰炸。希氏夫妇的房子是西式建筑,比一般民房坚固,所以每天有许多人跑到他们家躲避轰炸,屋子里打满了地铺。在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怀有身孕的露易丝接受美国领事的命令前往厦门居住。就在广州沦陷后一个星期,他们的第三个孩子诞生了,这是一个男孩,露易丝为他取名为“祝虔·班顿·希”(Eugene Benton Hill),没过多久大家都叫他“小虔”(Little Gene)。
由于日军的侵扰,安全堪忧,露易丝只好带着婴儿从厦门转往香港避难。希祝虔牧师则继续坚守在广州东山郊区,利用自己美国人的身份,成立“救饥中心”,救助了无数的难民,同时他也把福音传给患难中的人们,使人克服战争的恐惧,带给人希望与平安。当时西方宣教士已全部撤离,整个东山区只剩下他一个“洋人”。每个礼拜日,希祝虔除了在东山教堂,还要去其它几个教堂讲道,他更要尽力地保护当地的百姓。有一天,他得知沙河安老院有一批七、八十岁的老妪,每天都遭到日军们的强暴,再加上没有食物,许多人已奄奄一息。他就亲自开着卡车到安老院,把这些老人接到两广浸信医院,安置在隐秘的地下室里住下。有一次,日本兵到医院里搜寻,对着希牧师大吼大叫,并用刺刀刺伤他的身体,顿时血流如注。为了保护这些老人他险些丧失自己的性命。
1940年,希祝虔与妻儿回到美国度假。但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的宝贝儿子小虔不幸从五层楼窗口坠地身亡,当时他还不到两岁。万分悲痛中,他们把小虔葬在俄克拉荷马的祖坟内,然后希祝虔仍按照原计划到肯塔基的神学院进修。长期劳累,再加上巨大的丧子之痛,希祝虔终于病倒了。医生检查之后,发现他已患了严重的胃溃疡,情形非常危险。为了能使身体尽快复原,尽早回到中国宣教工场,他们接受安排,到气候比较温暖的德州圣安东尼奥去疗养。后来他的胃被切除只剩下原来的四分之一。
1940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把美国卷入了世界大战。由于局势紧张,希氏夫妇一时无法前往中国。他们只好先回到俄克拉荷马州待命。1941年9月1日,露易丝又生下了一个男婴,取名约翰。虽然喜获麟儿,希祝虔仍然忘不了他在广州的主内弟兄姊妹,一直焦虑地等待时机奔赴中国。一直到1945年8月,希祝虔才拿到护照。但这次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成行,因为露易丝和小约翰的护照未被批准。
希祝虔是战后第一批回到中国的宣教士之一,也是第一个回到广州东山的人。当时的广州百废待兴,一人要当十人用。由于人手奇缺,希祝虔只好临时兼任校长,担负起恢复两广神道学院的重任。1946年,西方宣教士陆续回到中国,露易丝和小约翰也于同年6月来到希祝虔身边。当时“两广浸联会”的主要事工是教育。1946年9月,秋季开学的时候,在东山的本校、以及在邻近诸省分校的学生,包括高中、初中、小学和幼儿园,总共有8500多学生。不幸的是,国共内战又起。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接管政权之后,西方各国差会纷纷撤离。希祝虔夫妇所属的“南中国宣道会”(South China Mission)决定留守不动,希祝虔一家也继续留在东山。广东解放后,形势完全改变。共产党军队占据了东山校园,还利用校园广播站进行宣传。学校的教职员工都要被集中接受政治教育。最后,中国政府向所有外国宣教士下了逐客令,希祝虔一家于1951年离开他们所爱的中国。
回国后,希祝虔的身体状况很不好,必须要彻底休养,医生停止他演讲和讲道六个月之久。待身体复原后,他马上到各处演讲,让大家了解在中国所发生的事情。他和露易丝虽然心系中国,但中国的大门毕竟是关闭了。不久,海外差传部决定开拓新加坡——马来亚地区,希祝虔夫妇成为最佳人选。1951年10月,他们再度搭上威尔逊总统号,经日本、菲律宾到达香港;再换乘一架小型飞机抵达新加坡。希祝虔在新加坡最早的福音据点在甘榜士叻(Kampong Silat),吸引当地许多青年人,很快教会就兴旺起来。不久,一对从香港神学院毕业的年轻夫妇——麦希真和陈永萱,应召前来,成为希祝虔的同工,并成为该教会的牧师和师母。麦希真牧师日后担任新加坡神学院院长,成为普世华人教会的名牧。
在希祝虔夫妇到达新加坡以前,新、马地区只有三间浸信教会。他们的到来,是美南浸信会在东南亚工作的起步。作为行政主任,希祝虔穿梭往来于新、马各岛屿、城市、乡村和丛林,开拓工场、建立教会、布道、主领圣餐、为人施浸、以及带领各种聚会。在东南亚五年期间,由于过度的劳累,希祝虔曾发生三次严重的胃出血。有一次他连续流了几天的血,昏迷不醒,以至于连医生都放弃了,交待露易丝去准备后事。后来虽然奇妙地恢复了,但需要较长时期的休养。直到总会差派提普敦夫妇(Dr. & Mrs. Tipton)接替他们的工作,希祝虔一家才不得不回美国休息。
1955年6月,希祝虔一家在归程中,顺访圣城耶路撒冷。回到得克萨斯州后不久,希祝虔接受医生的建议,再次做了胃切除手术,此后他的健康情况明显地改善。总部安排他去維吉尼亚州,负责总会中宣教教育部门(Department of Missionary Education)的工作。他一上任,就和露易丝马不停蹄地到各处演说,介绍东南亚的宣教工作。他的工作包括策划宣教工作、招募新宣教士、募款、编印发行各类期刊、与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宣教士们的联络通讯,以及供给他们所需等等。在他任期内,宣教教育部扩展了一倍;他也曾作了四次的海外旅行。
1975年底,希祝虔年届65岁时,正式申请了退休。晚年专心致力于在华人中间的宣教和牧养工作,成为华人的好牧师、好朋友。他帮助列治文华人教会建教堂;帮助在维吉尼亚州、马利兰州一些华人教会成长。他曾为列治文的华人主持了27个婚礼和72个丧礼;他甚至帮助华人办理各样琐碎事务,包括到法庭作翻译,协调纠纷等。希牧师可说是在列治文的华人中,阐释基督之爱最完备的一个人了。他虽然是一个资深的宣教士和教会领袖,但总是默默地作着幕后的工作,许多人都深深地被他柔和谦卑的样式所感动。希祝虔那温煦而又诚实的人格像磁铁一样,把来自各个不同背景的华人,紧紧地吸引在一起。
1989年夏天,列治文华人教会开始计划建堂,并为此选出一个建堂委员会。最初教堂的草图是由希祝虔设计的,再经由在大学中教授美工设计的容灵光先生把它勾画成透视图。据容灵光弟兄说,当他要把完成的透视图拿出来时,非常的紧张,因为他把希祝虔草图中的许多地方都更改了,很担心希祝虔看了会不高兴,没想到,希祝虔看了非常的喜悦,直夸他画得好,他心中的一块大石头才落地。虽然在委员会中没有哪一个人比希祝虔更适合做主席的了,但是,自从他在中国大陆时开始,就一直祷告期望在中国信徒当中,兴起领袖人才来为主做工。所以,他自始至终都扮演着配角,为的是要让华人弟兄们,有更多操练的机会。虽然,在建堂的舞台上,希牧师甘居幕后,但实际上,他是最为忙碌、也最为重要的人。他不但为维州浸联会和列治文浸联会,游说到两笔最大的贷款,平时到其它美国教会聚会或讲道时,也不忘为华人教会建堂募些款项。由于他如此默默地付出与耕耘,许多会友都以不具名的方式,奉献出他们的存款。在美国建房子,所要交涉的官僚机构很多。由于建堂委员们平常都要上班,没有时间与这些机构交涉,于是希祝虔便扛起了这些令人无奈,却又非做不可的事情。光是为建筑许可这一件事,他就往四十分钟路程以外的郡公所跑了五十次左右。那里的办事人员看他每天坐在旁边,为华人教堂的建筑许可耐心地等待着,便对他说:“你可骗不了我们,你是一个中国人准没错!”除了郡公所以外,其它与电力公司、电话公司、消防局、环保局、包工等的联络事项,也都是他在跑腿。大家看他如此辛苦,都劝他多保养自己身体,注意休息。但是他说:“你们还有时间,我却没有了”。
当一切准备就绪,终于举行破土典礼后,希祝虔便成了全天候的监工,每天督促包工,查验各项工作是否作得完善,结果仅用半年时间,整个教堂便差不多完工了。1991年10月12日,列治文华人浸信会举行了献堂典礼,参加的人数近三百多人。许多会友都忍不住喜极而泣。此前希牧师自己曾说:“列治文华人教会将是神交给我的最后一件工作了”。
1992年圣诞节临近时节,冰雪交加,气候寒冷。12月10日那一天,希祝虔在家里准备讲章,因为他要于12月13日主日到诺福克的第一华人浸信会讲道。午餐后,他和露易丝开车出去买东西,回家的路上,因路滑车子失控,不幸与一辆货柜车相撞,致使他自肩膀以下的身体都失去知觉。但他的头脑一直清醒,还一再关心妻子是否受伤,并关照她说:“你要打电话给艾伯·刘,告诉他我礼拜天不能去了。也许你可把我写好的信息寄给他,他可以念出来,它就放在我的桌子上”。不久,希祝虔在马利兰州的长孙艾伦和他的妻小,在波士顿的次孙布鲁士,以及教会的牧师和几位会友都先后赶到医院。在众亲友的祷告及交谈中,希牧师渐感呼吸困难,于当日晚9:30分安详地闭上眼睛,离世与主同在了。在世享年82岁。
希祝虔的追思礼拜在星期一举行,礼拜程序单上面写着的却是“庆祝希祝虔牧师的一生”(In Celebration of the Life of Dr. Eugene L. Hill)。许多与会人士穿著的不是黑色的礼服,而是色泽鲜艳活泼的衣服。可容纳近千人教堂里坐满了黄皮肤、白皮肤和黑皮肤的人,这是希牧师那超越种族的爱把这些人凝聚到一起的。所有认识他的中国人皆深有同感:他比我们中国人更爱中国人,也更能为中国人牺牲。他爱中国人是如此之深,以至他入殓时,身上穿著的是那袭他最喜爱的长袍马褂。追思礼拜最后由孟渝昭牧师以国语祝福结束:“正如当年以利亚离去时以利沙所作的祷告一样,愿主将赐给希老牧师勤恳、忠心、爱主的心,尤其爱中国人灵魂的心志,更加倍的赐给我们。阿们!”在《列治文新闻快递》报纸上一则报道中,引用了一段列治文浸信联会主席查尔斯·南恩(Rev. Charles B. Nunn)的感言:“希祝虔虽然有一个盎格鲁(白种人)的身体,内里所包藏的却是中国人的灵魂”(He may have an Anglo body, but he had Chinese spirit.)。
资料来源
- 金幼竹著,《心系中国——希祝虔牧师一生纪行》。台北:宇宙光全人关怀,2006年初版。
关于作者
作者蔡国栋是美国加州美福神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