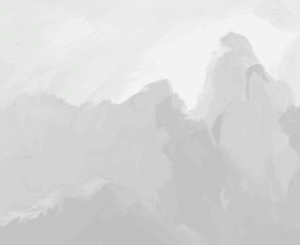基督教思想家、哲学家和文学家。自幼熟读中国传统文化经典,深受中国传统思想及佛教影响。青年时期先后留学于日本的高等师范学校、立教大学;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归国后,他先后执教于广州岭南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金陵大学和香港浸会书院等大学。生平著作和译述甚丰,晚年在美国参加了《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之翻译。
谢扶雅(Nai Zin, Zia)于1892年6月29日(光绪十八年六月初六),出生在浙江省绍兴府山阴县昌安门外昌蒲溇村,乳名谦,谱名祖光(取《易经》中“谦尊而光”),按辈分名为镇竟,在家里排行第二。13岁时,九堂叔以古文“夫(扶)惟大雅,卓而不群”中的“惟大”(《汉书·景十三王赞》)作为学名,“扶雅”为字。留学日本时,谢扶雅按堂兄的名字“乃绩”排字,为自己取名为“乃壬”,他的英文名Nai Zin Zia(简写为N. Z. Zia)就是根据谢乃壬音译过来的。
谢扶雅的父亲谢昌衢是晚清一名秀才补廪,以开馆授徒为生。在谢扶雅两岁时罹患伤寒,英年早逝。留给幼年谢扶雅的唯一印象是他坐于父亲膝上,观其批改文卷一丝不苟。谢扶雅的母亲万纫芳27岁守寡,在穷乡僻壤,含辛茹苦地抚养四个幼小的孩子成长,其艰难处境可想而知。困顿中的慈母总在危难时昼夜绕室徬徨,口念喃喃佛号,呼求于菩萨。她的柔肠百转,她的忧苦表情,她的虔心吁祷,给年幼的谢扶雅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后来觉得正是母亲这份宗教虔敬的态度,在他的灵魂深处埋下了宗教信仰的种子。
谢家和谢扶雅的舅家都是大户望族。父亲过世后,谢扶雅的童年生活虽然比较窘迫,却也能依靠典当旧物和叔伯舅父们的接济勉强度日。谢家是世代书香门第,谢扶雅从4岁起就在自家私塾中接受正规、系统而严格的传统教育,每天上半天课,5岁开始了全日制的课程,这样一读就是十年。从三字经、诗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到尔雅、书经、易经、礼记、春秋左传,再到国语、国策、史记等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童年的谢扶雅都能熟背如流。传统文化的薰陶使谢扶雅受用终生,成为他建构其思想学说、阐述中国文化及基督教教义的基础。
1905年,谢扶雅13岁时参加县考,未能考中。十年苦读,并未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美梦。1906年,清廷废科举,办学堂后,谢扶雅参加了绍兴中西学堂的录取考试,并荣登榜首。但终因他无力承担食宿等费用而放弃这次接触西学的机会。那年谢扶雅的舅父到江苏省溧阳县任钱谷师爷,他跟随舅父到江苏学习大清律例。既然科举无望,中西学堂也未去成,谢扶雅想试试读律这条路,希望能找到一份安稳的工作以糊口,或者还可以成为一个绍兴师爷。但却因舅父吸食鸦片成瘾,且不擅长训练后进而丢掉饭碗赋闲归家,谢扶雅也因此失去营生,白白耗掉了三四年大好青春年华。他后来曾作词自嘲曰“读书读律两无成”。
18岁那年,谢扶雅寄食于九堂叔府中,为其代修家书。适逢九堂叔之母逝世,在帮助料理杂事之时,他遇到从日本留学归国度假的远房堂兄谢乃绩。言谈中,堂兄感慨其弟具有如此聪颖之才华却陷于穷途末路之境地。于是劝谢扶雅东渡日本求学。1911年初,谢扶雅去苏州向大舅母借了30元留日之路费,踏上了由上海驶往日本横滨的航船。经过一个月的漂泊,抵达日本,在东京堂兄处落脚。求学期间所需费用也由其堂兄支撑下来,谢扶雅的人生出现了转机。
初到日本,谢扶雅先到一家日语学堂学习日文。一年多后,他完成了日语的初高级课程,报名进入东京郊区的同文书院学习。期间,谢扶雅被推选为同学会的会长。1912年3月,谢扶雅由同文书院毕业,获得了他平生第一张也是唯一的文凭。
为了备考日本的官费高等院校,谢扶雅搬到早稻田大学附近的留日学生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分会宿舍,在这里他生平第一次真正接触到基督教信仰。在此期间他与早稻田分会的马伯援成为至交,并结识了诸多基督徒朋友,其中给他印象较深的是同学罗文光弹唱的圣诗。这些圣诗常常使他感动,使他想起母亲在宗教上的虔诚。1913年谢扶雅感染“奔马性”肺结核,医生告知其好友罗文光说他只有两三个月的寿命。罗文光隐瞒此事,陪同谢扶雅在海滨休养一个多月。后来他的肺结核不治而愈,只留下钙化点在X光片上。
1914年4月,谢扶雅考入了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获得了官费资格。但年青的谢扶雅竟因一次考试中的作弊行为,而遭到退学处分。后在朋友的帮助下,谢扶雅在1915年秋转学到教会办的立教大学读书。在此期间,他的视力急剧下滑,被医生诊断为急性视网膜炎,后来转为慢性。医生建议他不能再继续读书,但谢扶雅仍然坚持不辍。在一次治疗过程中,一名护士因为给他注射错药物,跪求他的原谅。这个经历使他突然感受到上帝的仁慈与宽恕,想起童年时母亲曾经为在病床上的弟弟祈福的形象,好友罗文光所弹奏的圣诗,使他产生了皈依基督的渴望。于是,在基督徒好友罗文光和郑天民的陪同下,谢扶雅于1916年春在一间圣公会的三一教堂,由美国牧师施洗,成为一名基督徒。多年后他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认为,他的受洗,看似偶然,实在是“瓜熟蒂落”的结果,因为这和几个基督徒朋友的人格感召,加之从小母亲的宗教虔诚在心中埋下的信仰种子是分不开的。
受洗后的谢扶雅,经常到教堂参加各种礼拜、聚会和宣道活动。在一次布道会上,他遇到了前来日本布道的丁立美牧师。时任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附属学生立志布道团干事的丁立美听说谢扶雅的写作颇具文采,遂竭力敦促他回国从事文字布道。丁立美牧师的建议,使谢扶雅认识到这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他有较强的文字才能,在日本期间就曾为多个报刊投稿。如今又因为生病,在日本无法继续学业。于是,谢扶雅接受了丁牧师的建议,于1916年秋天结束留日生涯,回国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China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从事文字工作。他主编《同工》等杂志,执笔一年一度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事工报告》,并撰写《基督教青年会原理》、《环球基督教学生同盟》等著作,也时常为《青年进步》等刊物投稿。1917年他为青年会和中华书局翻译了富司迪(Harry E. Fosdick)的《祈祷发微总论》(Comments of the Meaning of Prayer)、《完人之范》(The Manhood of the Master)和《培根文集》(Francis Bacon’ Essays)等著作。
1918年秋,时任青年会总干事的余日章将谢扶雅调到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总务部(General Administration)任文书干事。作为余日章的中文助理,他多次参与募捐及各项社会服务活动,协调各地青年会的工作,为青年会贡献自己的力量。而青年会积极向上、通力协作的工作氛围和精神,也使谢扶雅在知识和德行上受到薰陶和影响。他认为在青年会全国协会工作的这段时间,是他毕生工作中最没有人事纠葛、心情最愉快的时期,堪称他人生的第一个高潮。
1925年,由于谢扶雅在青年会的工作表现,余日章将基督教青年会北美协会给予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出国深造机会给了他,派遣他到美国学习两年。同年11月,谢扶雅奔赴美国。这可说是谢扶雅人生的又一次重大的转机。这个转机使他开始构建自己的哲学和宗教思想,而这个构建则是因为他到美国后接触西方哲学思想所引发的。
谢扶雅到美国后,先进入芝加哥大学的冬季学期学习,选修了神学院院长马绣诗(Shailer Mathews)的“社会神学”、史密斯(G. B. Smith)的“神学与哲学的关系”、海意腾(Augustus Hayden)的“比较宗教学”、爱姆士(Ames)和卫萌(Henry Nelson Wieman)的“宗教哲学”,以及米德(George Mead)的“哲学史”等课程。在此期间,谢扶雅还继另一位基督徒学者梅贻宝之后,被推选为留芝中国基督徒学生团契主席。
1926年秋天,哈佛大学聘请英国着名学者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前来教授自然哲学,谢扶雅得知后便转学到哈佛大学,在哲学系选修或旁听了许多著名教授的课程,其中包括新黑格尔主义的霍铿(William Ernest Hocking )、新实在论的培黎(Ralph B. Perry),以及谢扶雅最感钦佩、对其思想影响最深的英国哲学家怀特海(Alfred Whitehead)等人的哲学课程,以及穆亚兄弟(George F.and Edward Moore)的宗教哲学和宗教史课程。尽管谢扶雅并未完成任何学位,但他从怀特海等哲学大师那里所获得的收益却使他受用终生。他自认为在美国这两年的收获,要远远多于在日本六年的收获。1927年,谢扶雅从美国归来,为青年协会撰写了《人格教育论》与《宗教哲学》这两部著作,这是他深受西方哲学思想影响的产物。
1928年,谢扶雅在岭南大学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并于三年后主领岭南大学哲学系。在岭南大学期间,谢扶雅先后出版了《人生哲学》、《中国伦理思想ABC》、《伦理学》、《基督教纲要》、《个人福音》、《南华小住山房诗草》等著作,并主编《岭南学报》。另外他还邀请了诸多学术及文化名流来校交流或讲座,为青年学生开拓了视域,也提高了岭南大学文科在国内的声望。这些国内外的学术名流包括日本的井也边茂雄教授、哈佛的霍金教授、胡适之、张君劢等。岭南大学的执教生涯可说是谢扶雅人生的第二个高潮。
1934年暑假,谢扶雅带领一批岭南大学的学生访日,当他回国后看到城市和乡村的种种景象,深感于国家的忧患危难,以及农村的贫困落后。但他同时又体会到中国的潜力恰恰在于乡村。于是他撰写了“基督教对今日中国的使命”、“中国前途的杞忧”、以及“中国前途的预测”等文章,大声呼吁、号召广大青年到乡村去。谢扶雅以身作则,于1936年辞去岭南大学教职,远离象牙塔赴河北定县试验区,担任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秘书主任。他随平民教育促进会辗转长沙、遂川、成都、重庆等地,帮助地方干部培训工作,投身到乡村的平民教育事业中去。他出版了民众小丛书上百种,曾协助晏阳初编纂《千字课》识字教材及参考书,试图将百姓从愚、穷、弱、私中解救出来。1937年谢扶雅撰写了《基督教与现代思想》这部著作。
1939年,谢扶雅重回岭南大学任教。由于受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抗战期间他不得不辗转执教于各地。1940年,谢扶雅担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长兼文学研究所主任。1941年应院长廖世承的要求,他出任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公民训育处主任。1943年又担任东吴大学训导长兼主中国文学系。1944年,谢扶雅翻译了鲁一士(Josiah Royce)的《宗教哲学》(Religious Aspect of Philosophy)一书。1945年谢扶雅到桂林西江学院任教。抗战结束后,谢扶雅抵达重庆,在乡村建设学院任职社教系及国立编译馆。1946年6月,他又随国立编译馆迁到南京,之后在金陵大学教课。1947年,谢扶雅又主编了哲学丛书,编撰《道德哲学》。
谢扶雅带着他的西方哲学理念,历经国难,颠沛流离。作为一位书生,在民族危难之际,他只能用自己的笔为困顿中的人民呼喊,鞭挞侵略者的罪恶行径,唤醒国民的觉悟。他出版了大量著述、教诲了大批青年学子,同时还身体力行地参加了乡村建设运动。在这一时期,对谢扶雅而言,是思索自己哲学体系的时期,并且也是将自己的思考付诸于实践的时期。他坚持对中西宗教思想、中西哲学文化进行一种比较研究,认识彼此之“异”,互补互长、吸取精华。又认识彼此在根本点上之“同”,从而发觉融会贯通,铸成新体的可能。而此时的思考是以他对人生及道德哲学的思想开始的,其立足点已经逐渐从西方哲学的视野转移到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价值因素的发掘上来,将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信仰借由一种中国式的阐述表现出来。
1948年9月,谢扶雅担任湖南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后为躲避时局的混乱,他再抵广州,到华侨大学任教育系主任,并在岭南大学兼授人生哲学。1949年7月,谢扶雅离开广州,奔赴香港。最初他受岭英中学校长洪高煌的聘请,在岭英书院主持国文系,并在教育系开设伦理学一课。一年后,岭英学院因财政困难而停办。1952年他任教于香港政府开办的文商专科学校;1953年谢扶雅在刚刚成立的崇基学院教授国文和中国哲学史。1956年,谢扶雅任教于新成立的香港浸会学院。在香港期间,谢扶雅撰写了《当代道德哲学》、《人生哲学》、《中国政治思想史纲》、《中国文史述评》和《伦理学》等著作;同时还为《崇基学报》、《青年文友》、《人生》、《景风》和《光与盐》等杂志撰文。
虽然在香港的生活及工作已经打开局面,但谢扶雅认为香港的社会现实,对他并不适合。1958年4月,谢扶雅应纽约金陵神学院托事部主持的邀请,离港赴美,进入《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编译所工作,开始了他近二十年的翻译生涯。在此期间他先后编译了《基督教早期文献选集》、《东方教父选集》、《中世纪基督教思想家文选》、《圣多默的神学》、《安立甘宗思想家文选》、《不列颠宗教改革思潮》、《康得的道德哲学》、《近代理想主义》、《祁克果人生哲学》、《士来马赫:宗教与敬虔》、《虔诚生活——许革勒文集》等多部译作。他还撰写了《基督教与中国思想》,翻译了教会史家根·司各脱·来德里(Kenneth Scott Latourette)的《耶稣纪元》,翻译名作《自有耶稣以来》。此外,还有一些短文,如“唯中论:中国特有的哲学”(载于《东方》杂志)、“新唯中论发凡”(《海外论坛》),以及“个性、偶性与众性”(《海外论坛》)等。
谢扶雅以垂暮之年,花费近二十年精力,将西方宗教和哲学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部分译成中文,这是他人生的第三个高潮。此时身处于异质文化中的谢扶雅对于中西文化融合及其途径有了更深入的体认,他站在一个基督徒的立场上,创立并完善了他的新唯中论的哲学体系,发挥了他的“不偏不倚、执两用中”的中和神学思想,提出了他的“以行体信”、“中和的逆证”等本色神学构想。他所撰写的《基督教与中国思想》这部作品以及“中国基督教初论”、“中华基督教神学的几个原则”等文章充分阐述了他此时的宗教及哲学观点。
1970年,谢扶雅出版了自传《巨流点滴》。之后在他80岁时,在友人的鼎立相助下,收集并整理了他的三百余万字的文稿,出版了六卷本的《南华小住山房文集》,卷一:《人生哲学》、《道德哲学》、《中国伦理思想述要》、《中国政治思想史纲》;卷二:《经义讲义纲领》、《中国文学史论》、《修辞学讲义》、《中国历史闻人月旦》、《生活指导课本》、《学术论文选集》;卷三:《宗教哲学》、《基督教纲要》、《基督教与现代思想》;卷四:《中国宗教思想论业》、《基督教与中国》、《基督教历代名著导论集》、《证道、灵修、及其他》;卷五:自五四至抗战前夕,抗战时期及复员、大陆易权以来各个不同时期的时论;卷六:诗作及杂文。文集收录了谢扶雅本人的大部分著述,从中可以找寻其思想发展的轨迹,并且领略他的文学、哲学和神学风采。
晚年的谢扶雅双目失明,但他仍凭触觉,笔耕不辍。他这段时期的论文多收录于《生之回味》、《周易论集》、《谢扶雅晚年文录》、《谢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等多部著作中。1980年,近90高龄的谢扶雅应台湾当局的邀请访台,并到东海大学及多所神学院作学术讲座。1983年谢扶雅回国探望,先后在中山大学及北京、南京、上海等多所高校及研究机构讲学,受到中国政府的热情款待。三个月后,谢扶雅返回美国,曾一度与他人合办《海外中华》杂志,但终因年老体力不支而停刊。1986年9月,谢扶雅返回广州定居。1991年6月13日,百岁的谢扶雅邀请了亲友和家人在广州的白云宾馆餐厅庆祝其一百荣寿。三个月后,谢扶雅逝世于广州。
谢扶雅是华人神学界的传奇人物,他除了具备坚实深厚的国学训练外,更对基督教的传统有丰富的认识。他对中西文化的比较研究,更是他对中西哲学的融会贯通;而他在宗教哲学的论述更是高瞻远瞩,比很多西方的宗教哲学家早了数十年,率先突破那种将宗教哲学化约为基督哲学或西方宗教哲学的既偏且狭的进路,代之以一种跨文化、跨宗教的进路。[1]
谢扶雅经历了由民国成立至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等重大历史转变,并在海外生活过很长的时间,在面对大时代的种种社会变迁,以及离开本国本土的离散经历,谢扶雅的神学思考有着强烈的时代印记。他漂泊一生,使他自身的信仰、民族、文化身份构成了他的中华基督教神学的思想泉源。
纵观谢扶雅的一生,他童年时父亲的过早离世,年轻时的体弱多病,中年时的流离失所,以及老年时的离乡背井,无不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百多年中多灾多难的经历。也正是这样的遭遇,使谢扶雅在人生几次关键时刻的选择都带有几分无奈,包括他因病从日本回国,1949年去香港,1959年去美国,在加入美国藉后,又在高龄时选择回广州定居。由于他生活和工作环境的不断改变,他的思想,以及他对信仰的认识多少有一些在离难中,因境遇变迁而夹杂的不十分准确的因素。从其信仰和神学思想判断,谢扶雅不是个传统意义上“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而更像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基督徒”。他在晚年的时候多次在文章中提到自己皈依基督与童年母亲在观音面前迫切呼求祷告有关联,以及把中国的诗、书、礼和孔墨老庄比喻为旧约,“而可接通至耶稣基督的‘恩典时期’的新约”(《谢扶雅晚年基督教思想论集》210页),甚至把他八十年代重返大陆访问时统战部人员在他面前的道歉和改革开放搞经济与圣经的“人要重生”联系起来,比作痛悔前非的表现。此外他的“中华基督徒”和中国本色神学等观点,也是见仁见智。因此他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基督徒也就不足为怪了。也许正如他自己所说:“回眸一生,感慨自己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基督徒,至多只能称为一个‘有思之士’”。
脚注
何庆昌,《谢扶雅的思想历程》,第xi页。
资料来源
- 谢扶雅著,《巨流点滴》,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1970年。
- 何庆昌著,《谢扶雅的思想历程》,台湾基督教文艺出版社,2013年。
- 网路资料:唐晓峰,《谢扶雅先生小传》。
- 百度人物词条。
关于作者
作者系美国加州基督工人神学院硕士研究生,在李亚丁教授指导下撰写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