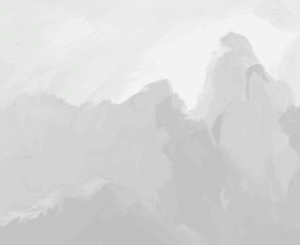1834年8月1日,第一位來華基督教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病逝後,為紀念他對華宣教之貢獻,在英國商人查頓(William Jardine)、顛地(Laneelot Dent );美國商人奧利芬(David WC Olyphant),以及傳教士裨治文(Elijah Bridgman)和馬儒翰(John R.Morrison)等人的倡導和推動之下,開始籌建“馬禮遜教育會”(Morrison Education Society)。 1836年9月,馬禮遜教育會在廣州正式成立,其宗旨是在中國開辦學校,改進和推動中國的教育。在這些學校裡除了教授中國學生中文外,還要教授他們讀寫英文,並以此為媒介,向他們傳授西方世界的各種知識。這些學校還要求學生讀《聖經》和有關基督教的書籍,希望“在不遠的日子裡,看到中國人不但為了商業、知識和政治的目的與歐美國家交往,而且在拋棄了他們的反感、迷信和偶像之後,同基督教國家的人民大眾一起,承認和崇拜真神上帝”[1]。馬禮遜教育會一成立,即致函英美兩國教會和教育界,希望他們物色、差派合適的教師來華辦學,得到美國方面積極回應。在耶魯大學三位熱心教授的力荐下,該校畢業生布朗(Samual Robbins Brown)表示願意來華辦學。
一、早年背景
布朗於1810年出生在康涅狄克州的東溫莎鎮(East Windsor, Connecticut),早年畢業於馬薩諸塞州的孟松學院(Monson, Massachusetts),隨後進入耶魯大學深造,於1832年畢業。 1836年,布朗又先後在南卡羅萊納州的哥倫比亞神學院(Colombia Theological Seminary)和紐約協和神學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 New York)攻讀神學,畢業後在紐約一個聾啞學校當教師。 1838年,布朗被按立為牧師;同年10月與伊麗莎白•巴特萊特(Elizabeth Bartlett)結婚。
布朗是一位信仰虔誠、學識淵博,且具有宣教熱情的人。耶魯大學校長在推薦他到馬禮遜學堂任職時,給予他很高的評價:“布朗先生在我校完成了四年的正規學習課程,1832年獲得文科學士學位。在校期間,他的聰慧敏捷、多方面的才能和文雅的舉止都是出類拔萃的。對學校開設的每一門課程,他都保持優良的水平。他平易近人,令人喜歡;他那種高尚情操和作為一個虔誠基督徒堅韌的生活和性格為人所尊重。”[2]
二、馬禮遜學堂
1838年,布朗接受了馬禮遜教育會的邀請,偕新婚妻子啟程去中國,從而成為第一位以教師身份來華的美國人。他們在奧利芬的資助下,於1838年10月17日從紐約搭乘“馬禮遜號”商船前往中國。經過四個月的航行,於次年2月19日到達廣州,受到馬禮遜教育會秘書裨治文的歡迎。四天后他們轉往澳門,一邊學習中文,一邊籌建馬禮遜學堂。經過一年多的籌款、準備和招生,馬禮遜學堂(Morrison Memorial School)於1839年11月在德國傳教士郭實臘(Karl Friedich August Gutzlaff)夫人溫施蒂(Wanstall)所辦女子私立學校和男塾的基礎上建立起來,布朗由此成了馬禮遜學堂的首任校長,也開了中國近代教育之先河。
1839年11月4日,布朗開始給學生上課,標誌著馬禮遜學校在澳門大三巴附近正式開學。首批學生只有5名,即黃勝、李剛、周文、唐杰和黃寬,1840年又有容閎入學。容閎回憶道:“予等六人為開校之創始班,予年最幼。”[3]這些學生均來自貧苦人家,年齡大者15歲,小者11歲。這6名學生全部住校,不僅學雜費、書費、食宿費全免,而且學校還負責提供衣被和醫療服務。馬禮遜學堂是個全日制學校,課程除了學習《聖經》和基督教基本教義外,還開設算術、代數、幾何、生物學、地理學、化學等等西方科學知識,英漢雙修。此外,學校也設有中國傳統的儒家經典,如《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以及四書五經等類課程。馬禮遜學堂建立伊始,就展現出與中國傳統私塾截然不同的風貌,體現出全新的教育理念。據1840年4月布朗寫給馬禮遜教育會的書面報告稱:“馬禮遜學堂……目標是在德育、智育和體育三個方面給予學生全面的訓練。按照這個目標,我安排中國學生半天讀中文,半天讀英文。早上六點鐘開始活動,晚上九點鐘結束。期間讀書共八個小時,餘下的三四個小時讓學生們到戶外場地上運動和娛樂。”[4]
布朗還寫道:“我讓學生們和我的家庭融合在一起。待他們如同自己的孩子,鼓勵他們對我們具有親密無間的信任,成為我們最好的朋友。他們可以自由地參加我們家庭的早晚禮拜。”[5]布朗說到做到,他和他的妻子在生活上關愛學生,在教學上又極其認真。在容閎和同學們眼中,“勃先生(指布朗),一望而知為自立之人,性情態度沉靜自若,遇事調處秩序井然。其為人和藹可親,溫然有禮;且常操樂觀主義,不厭不倦,故與學生之感情其佳。其講授教課,殆別具天才,不須遠征,而自能使學生明白了解。此雖由於賦性聰敏,要亦閱歷所致。蓋當其未來中國、未入耶魯大學之前,固已具有教育上之經驗矣。故對於各種學業,無論其為華人、為日人、或為美人,均能審其心理而管束之。知師莫若弟,以才具論,實為一良好校長。”[6]在布朗的言傳身教下,學生們進步很快,在該校學習三四年之後,除了熟悉中文外,對英文的聽、說、讀、寫都有了相當的基礎,並對世界各國的地理、歷史,乃至自然科學和音樂美術等學科都有所涉獵,而這些對那些讀中國私塾的同齡學生來說,是連想都想不到的事情。
布朗來華後,經過一段時間對中國語言文化的學習與考察,洞察到中國傳統教育之弊端:“僅僅是為了替政府培養一批勤勉而又保守成性的僕人。教育的目的不是使人的個性得到充分和自由的發展,學校的學習內容是一成不變的,自然科學知識被排斥在教學之外,獨立思考的精神受到壓抑。”[7]基於此,他主張在馬禮遜學校裡,一方面要強化漢語教學,另一方面要積極用英語講授、傳播西方文化,同時也開設基督教課程,鼓勵學生參加基督教活動。
在漢語教學方面,從布朗在馬禮遜教育會1840年年度報吿中,可對當時漢語的師資和教學情況了解一二:“一位倍受尊敬的中國長者受僱為老師,他的生活習慣和舉止行為與其教師身份相稱,成為學生的榜樣。他的漢語教學方式非常值得信賴。……學生們花費一部份時間來背誦中國典籍,同時他們理解中國經典的能力也增加了。” [8]學生主要是學習《四書》、《易經》、《詩經》、《書經》等典籍。至於學生學習漢語的情況,布朗在1842年教育會的報吿中也提及:“10名孩子已經背完或將近背完《四書》,並複習了它們。而高年級的一名學生,則已經學習朱子評《四書》,並努力理解它。他們中間大部份人理解《孟子》,理解孔子著作的人少了一些,而最難的《詩經》則無人能懂。他們中間有些人能將《孟子》中的段落翻譯成淺顯的英語。他們同樣在我的指導下,將中文版《新約》的段落翻譯成英語。”[9]由上可知,馬禮遜學校的漢語教育與當時的中國私塾教育大致類同,但布朗提倡班級教學,並在授課過程中增加講解經典內容的做法,使學生能夠取得較好的學習效果,這也是對中國傳統私塾填鴨式的教學方法的一大突破。
在英語及西方科技文化教學方面,學校開設有英語及用英文講授的天文、地理、歷史、算術、代數、幾何、初等機械學、生理學、化學、音樂、作文等課程,這是馬禮遜學堂的核心教學內容。對學生這方面的學習情況,布朗深感滿意:“在英語學習方面,他們取得了相當大的進步。他們中的兩人,在學完一本較小的著作之後,已接近完成一部有274頁的地理著作的學習。其餘4人正在學習上面提及的那本小型著作,並且學完了伯雷的地理著作的一半。在算術方面,他們先學習心算,然後學習戈登的書,完成筆算的基本內容:約數、複合加法、減法、乘法和除法等。每週他們要用上一天中的一些時間來學習寫作。在閱讀方面,包括講英語,在過去5個月獲得了顯著的進步。美魏茶牧師及文惠廉太太在我因訪問新加坡及馬六甲而缺席期間,在他們的訓練中大量地培養了他們的智力與誠實。我感覺到男孩們的品德也有了決定性的進展,比起先前我所見到的,他們更加誠實,更習慣於紀律,也更有良知,而且對他們所受的恩惠也表達出更多的謝意。”[10]布朗還指出:“馬禮遜教育會採用的教育計劃,彌補了中國教育系統所造成的每一個缺陷。我們為我們的學生打開了一個蘊藏在英語文化中的知識之源。”[11]
另外,從包括容閎和黃寬兄弟在內的第一班學生寫給裨治文的兩封信,以及他們的六篇用英文寫作的作文,可以側面了解學生們運用英文寫作的能力,以及對西方文化的了解程度。裨治文對那兩封信大為讚賞,並將它們登載在《中國叢報》上。而那六篇英文作文則是1845 年9月24日學校舉行的公開考試的一部分,題目依次為:《人生是一座建築,青年時代是基石》、《中國政府》、《勞動》、《一次幻想之旅》、《聖經》、《中國人關於來世的觀念》。當年舉行的學校考試,不僅考試科目比較多,而且非常嚴格。據史料記載,在這次考試中,年幼的學生要考英語閱讀、朗讀及口語翻譯;年齡較大的學生要考英文版的《新約》、地理、心算與幾何等課程。上述信函、作文及考試,是對學生英文水平的一次檢閱。事實表明,馬禮遜學堂的英語課程不僅僅是純語言性質,而是將近代西方科學知識課程納入教學範圍,“這些西學課程,全部採用英文課本,用英語教學。”[12]布朗的這一辦學實踐,既幫助了學生較快掌握英語的聽、説、讀、寫等基本技能,又有效擴展了學生的知識面。
作為一個教會學校,自然注重基督教教育,因為傳教士們的辦學目的之一就是“想通過學校來爭取眾多的異教徒男女孩童,使他們在基督教真理的影響下能夠皈依上帝,特別是成為基督福音的使者。”[13]學校向每位學生髮放《聖經》,在英語課程學習中以《聖經》作為教材,並在講授其他課程中也融入基督教內容,把基督教精神注入到各個教學環節。學校要求學生參加祈禱、禮拜儀式,以培養“具有基督教人格的中國學生。”布朗還積極營造一個基督教的氛圍,讓學生住在其家裡,與其一起參加早禱和晚禱,以“給予一個基督教家庭的教育。” 儘管學生大都未正式受洗,但他們在思想上對基督教普遍抱有明顯的好感。如一位學生如此寫道:“如果一個人對聖經一無所知,他就無法找到能引導他獲得拯救的靈光;他就會永遠處於黑暗之中,不知道自己會魂歸何處。……聖經教導我們救贖之路,真正的宗教將支撐我們渡過人生的種種磨難,面對最後審判的到來。”[14]容閎後來在美國受洗成為基督徒,與他早年在馬禮遜學堂所受的宗教熏陶是不無關係的。
鴉片戰爭結束後,馬禮遜學堂遷往香港,新校址在灣仔摩利臣山上,並且擴大了招生。 1842年11月,馬禮遜學堂在香港開始上課,新舊學生共20多人。到1843年,馬禮遜學堂的學生已增加到42人,分四班上課。此時學堂已擁有一個小型圖書館,中英文藏書已有4100多冊,學制確定為8年。學生仍來自香港、澳門的貧苦家庭,學費和膳宿費仍然全免。學堂的教學質量和學生素質均已大幅度提高。從 1839-1849年,除布朗夫婦在馬禮遜學堂任教直到1846年外,每年至少有一名中國教師講授中文。美國傳教士文惠廉(William Boone)夫人、哈巴安德(Andrew Happer)和邦尼(Samuel William Bonney),以及米憐之子美魏茶(William C. Milne)等人都曾先後任教或服務於馬禮遜學堂。
三、馬禮遜學堂之碩果
馬禮遜學堂早期學生都來自澳門、香港和廣東香山。後來又有來自廣州、南京、寧波和新加坡等地的學生。據不完全統計,馬禮遜學堂在其辦學10年裡,先後有50餘名學生前來就讀。儘管只有50餘人,但處於中西文化交匯點的這所教會學校,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乃至中國近代教育史上,卻佔有重要的地位。馬禮遜學堂培養了最早一批放眼西方世界,具有世界眼光的人才。這批畢業生對晚清時期西方文化在澳、港、粵乃至中國的傳播,做出了重要貢獻,其中一些人後來還成為晚清社會改革與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知名人物,如中國近代改良思想家容閎、近代首位西醫黃寬、近代中文報業的先驅黃勝,以及洋務運動中的重要人物唐廷樞等人。
1. “中國留學生之父”容閎
容閎於1828年出生於離澳門不遠的南屏鎮,家境貧窮。年幼時因讀不起私塾,才被父親送入這所不需交學費還管吃管住的教會學校讀書。容閎是六個孩子中年紀最小的一個。 1846年,布朗因其夫人久病不愈,需要回美國治療,故在同年9月30日馬禮遜教育會舉行的第八屆年會上,向教育會請求批准他一家回美國休假。獲准後即將離開中國之際,布朗深情地表示,願意帶幾個中國學生到美國求學。容閎在其用英文寫的自傳《我在中國和美國的生活》中憶及當時情景時,如此寫道:“布朗先生是在1846年冬天離開中國的。在他臨走之前四個月,有一天,他突然宣布了一個令全校震驚的消息,說由於他和他的家屬因健康不佳,需要回美國去。最後他說,他對學堂懷有很深的感情,並說他願意帶幾名年齡比較大的學生去美國讀書,直到完成學業。凡願意與他同去的,可以站起來。……這時,我第一個站了起來,隨後是黃寬,最後是黃勝。 ”那天晚上,當容閎把自己的決定告訴母親時,母親哭了。那時到海外去,很可能意味著生離死別,但母親最終還是同意了。為了免除家長與孩子的後顧之憂,布朗決定在三個孩子留美期間,定期給其父母匯寄贍養金。
1847年1 月4 日,容閎等三人在《德臣報》(China Mail)主編蕭德銳(Andrew Shortrede)、美國商人里奇(AA Ritchie)和奧利芬,以及蘇格蘭人坎貝爾(AA Campbell)的資助下,隨同布朗夫婦搭乘“女狩獵者”號輪船離開中國廣州。當時蘇伊士運河還沒有開通,輪船需要繞道非洲南端的好望角,故此他們共在海上航行了98天,於4 月12 日才抵達美國紐約。在紐約短暫停留數日後,布朗一行乘船前往紐黑文,參觀過耶魯大學後,再轉乘火車,最後抵達位於康涅狄克州東溫莎鎮的布朗家。
很快布朗將三個中國孩子安排進入馬薩諸塞州芒松中學讀高中,並讓自己的母親照料他們。三個孩子中的黃勝,因水土不服,在芒松中學讀了一年即輟學返回香港;而容閎和黃寬則讀完了全部課程。隨後,黃寬考入愛丁堡大學醫學院,前往英國蘇格蘭;而容閎則於1850年考入了耶魯大學。容閎進入耶魯時,全校有500名學生,只有他一個華人。 1854年夏,容閎獲得耶魯大學文學學士學位,成為第一個受過完整美國教育並取得學位的中國人。
容閎後來之所以被稱為“中國留學生之父”,既因為他是中國近代首位留美學生,也因為他是中國留學事業的拓荒者。
1854年冬,容閎學成歸國,成為最早的“海歸”,後來成為曾國藩的幕僚,辦理洋務事宜。 1870年,容閎向曾國藩提出了他的“留學教育計劃”——即由朝廷出資,選送幼童出國留學。他的建議得到了曾國藩的讚同與支持。經過近20年的努力,中國始向西方選派幼童留學。從1872-1875年間,清廷先後選派了三批幼童共120人赴美留學。雖然該幼童留學計劃後來因保守勢力的反對而夭折,但它畢竟開啟了中國學生出洋留學的大門,這件事在中國近代史上具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這幾批幼童學成回國後,不少人成為國家之棟樑,如詹天佑成了中國鐵路之父;唐紹儀,曾任民國第一任總理;唐國安,清華學校首任校長;梁敦彥,曾任清廷外務大臣;梁如浩,交通大學創始人。如果說容閎是中國近代的留學之父的話,那麽美國傳教士布朗就是將這位留學之父帶出國門的人。可以說,布朗改變了容閎的命運,而容閎又通過自己的努力推動了中國的留學制度,催生了中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批官費留學生,寫下了中國留學史上光輝的第一頁。
2. 中國西醫第一人黃寬
黃寬在蘇格蘭愛丁堡大學讀了7年醫科,在通過愛丁堡皇家外科學會的考試,獲得愛丁堡皇家外科學會的醫學博士學位證書之後,於1857年1月回國,成為畢業於歐洲大學中的第一位中國人,也是經過西方醫科大學正規訓練的第一位中國西醫,因此被尊為“中國人始留學歐洲習醫術者”。
黃寬將西方的先進醫學引入回國,是中國實施胚胎截除手術的第一人。他先後就職、服務於香港的倫敦會醫院、博濟醫院、廣州海關醫務處;任教於南華醫學校。黃寬在中國近代醫學史上有著獨特的地位,被譽為“中國西醫學的奠基人”。可惜他於1878 年12月因患頸癰疽去世,年僅49 歲。英年早逝,令人唏噓!
3. 近代中文報刊的先驅者黃勝
黃勝乃黃寬之兄,是跟隨布朗赴美留學三位學生之一。雖然他於1848年因病返回香港而沒能完成西方大學教育,但他後來在香港教會和社會十分活躍,曾追隨英國傳教士、著名的漢學家、教育家和翻譯家理雅各博士多年,協助他辦報、譯述、教學、從事教會工作和社會公益活動,因此被譽為“香港華人提倡洋務事業的先驅”和“近代中文報業的先驅”。理雅各在香港期間所取得的成就,可以說有黃勝的一份。
4. “中國民族保險業之父”唐廷樞
唐廷樞,馬禮遜學堂首屆6名學生之一,當時名叫唐杰。他從馬禮遜學堂六年畢業後,憑藉一口流利的英語,先後在香港和上海的海關及洋行任職,後踏入商界,成為著名的買辦。 1873-1886年間,李鴻章任命唐廷樞先後出任輪船招商局總辦和開平煤礦(今開灤煤礦)總裁,成為晚清洋務運動中的重要人物,也是李鴻章辦理洋務的重要助手,以致於李鴻章說出“中國可無李鴻章,但不可無唐廷樞”之語。唐還創辦了多家保險公司,從而被譽為“中國民族保險業之父”。
四、布朗餘生
因在中國七年之久,長期勞累,布朗夫人身體情況在短期內難以復原,故當休假結束後,無法跟隨布朗再去中國,布朗也只好留在美國陪伴妻子。加之馬禮遜教育會的實際負責人裨治文離開香港前往上海拓展事業,因此馬禮遜學堂在師資與經費缺乏的情況下,舉步維艱,只好於1849年春宣告停辦。
在妻子治病期間,布朗在紐約從事教育與辦學。待妻子病癒後,他們又前往日本,在那裡興辦西學長達20年之久。 1878年布朗再度訪問中國,在廣州受到馬禮遜學堂部分校友的熱情接待。黃寬等人出資並陪同布朗到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參觀遊歷。布朗在日本一直工作到1879年才退休回美國。 1880年6月20日,布朗病逝於馬薩諸塞州的孟松鎮(Monson Massachusetts),享年70歲。
腳注
-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0頁。
- Chinese Repository,Vol.10,第567-570頁。
- 容閎:《西學東漸記》第73頁,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 顧長聲:《傳教士與近代中國》,第40-41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同上。
- 容閎:《西學東漸記》,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74-75頁。
- Chinese Repository,Vo1.13,第631頁。
- 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112頁。
- 同註22,第131-132頁。
- 同註22,第112-113頁。
- 湯開建、陳文源、葉農主編:《鴉片戰爭後澳門社會生活記實》,花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頁。
- Chinese Repository,Vol.10,第569頁。
- 陳學恂主編:《中國近代教育史教學參考資料》(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 年版,第2頁。
- 轉引自史靜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與中國知識份子》,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69-70頁。
資料來源
- 容閎著,《西學東漸記》,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 Beauchamp, Edward R., "Brown, Samuel Robbins," Encyclopedia of Japan (1983). Drummond, Richard H., A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n Japan (1977). Griffis, William Elliot, “A Maker of the New Orient, Samuel Robbins Brown” (1902).
- 顧長聲著,《傳教士與近代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 網絡相關資料。
關於作者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