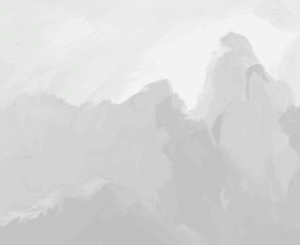一、早年生活與神的呼召
華理士(William Wallace)於1908年1月17日生於美國田納西州諾斯威爾城(Knoxville),父親是一個內科醫生。在他11歲時,一場流感奪去了他美麗賢淑的母親,剩下父親和外祖母照顧他和妹妹。他具有機械方面的秉賦,當其他同齡人開始醉心于體育、學業或社交之際,他卻埋頭鑽研機械,而且小有成就,因此他的親朋和家人都認為他將來必定會成為一個出色的工程師。然而,在華理士17歲時的一天下午,一向沉靜寡言的他卻怎麼也定不下心來做他喜愛的機械活計,仿佛內心有一股力量在不停地催迫他,讓他停下手上的工作,靜下心來認真思考生命的意義。一個問題不斷在他腦海中浮現:“神在我身上的旨意是什麼?”就在那一瞬間,華理士似乎清楚地聽到了神對他的呼召——“準備當一名宣教醫生,將來到我差遣的地方去傳福音!”1他隨即拿起打開的聖經,在頁邊的空白處寫下了自己對神呼召的回應。當時他並不知道日後神將會差遣他到哪裡去,但從那一天起,他就決志奉獻自己為主所用,定意要做一名醫療宣教士,並開始努力裝備自己。
高中畢業後,華理士進入田納西大學醫學預科,後在孟菲斯大學醫學院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在諾克斯維爾總醫院實習期滿後,留在該院擔任外科住院醫師。但就在他醫學院畢業時,他的父親去世了,家中只剩下他和妹妹路德兩人。
華理士生性靦腆,自己認為口才不好,不適合作教師。但他對宣教事業充滿熱忱,確信神將使用他作為一名醫療宣教士。他是一位和藹、誠懇的青年,常常是在幕後默默工作,但在他柔和謙卑的表現背後,卻有著一股很強的內在吸引力。1934年,華理士26歲,在諾克斯維爾總醫院作外科醫師時,他寫信給美國南方浸信會海外傳道總部,要求成為一名醫療宣教士,到有需要的地方去為主服事。奇妙的是,就在同一時刻,另一封來自中國廣西梧州的求助信也寄到了總部。由美南浸信會創立的思達醫院(Stout Memorial Hospital)院長畢濟時醫生(Dr. Robert E. Beddoe)向總部呼求,急需一名傳教醫生,而且一定要是外科醫生。因他罹患眼疾多年,已無法做外科手術,希望一位醫生能來接替他。畢濟時在信中代表那些在梧州所有飽受痛苦煎熬的病人呼求,請差派一名外科醫生來思達醫院。這兩封信同時寄到總部,從中可見神的旨意。
就在華理士開始準備去中國醫療宣教之時,卻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另一個頗有吸引力的邀請。他父親的老朋友,美國外科醫師學會一位資深會員邀請他來合作,成為行醫的合夥人。華理士很清楚這個邀請對自己將意味著優厚的高薪、醫學界“最前沿領域”的地位,以及前途廣闊的職業生涯等,這些都是一個年輕住院醫生夢寐以求的。這突如其來的大好機遇,對華理士來說是一個大誘惑。在其後的幾天裡,他一直為此事禱告。畢濟時醫生從廣西梧州給他寄來的那封信,一直在他腦海中:“我一直懇求總部派一名年輕外科醫生來,看來你可能就是擔當這個崗位的人選了。我盼求並祈禱這一願望得以實現。你的牧師極其熱情地寫信推薦你。如果你就是主所選定的那一位,我祈禱你能儘快到來。時間不多了,我們當趁著白晝,趕快作工。關於這裡的現狀,我可以足足寫上幾個小時,相信這樣或許更容易激勵你作出決定,但我的時間有限,而且我也不願意過於勉強你。我只能說,對於一個願意點燃自己生命去榮耀神的人,這實在是一個最不尋常的開端。我盼望你就是那一位。”2幾天之後,華理士再次來到老前輩的辦公室,把自己準備當宣教士的想法,一五一十地和盤托出。作為晚輩的華理士帶著他那為人所熟悉的靦腆神情,婉轉地謝絕了父親老朋友的盛情好意。
二、在梧州思達醫院之歲月
1935年,27歲的華理士辭別家鄉,坐上“柯立芝總統號”遠洋海輪踏上了去中國的征程。他終於看到了神在他生命中的安排——醫生、宣教、中國。到達中國後,華理士先在廣州學習一年語言,之後立刻開始在梧州思達醫院的醫療工作。雖然他在語言方面還存在一些困難,但他總是盡最大的努力學習,在行醫、拜訪病人時,盡力用粵語與人溝通,並以極大的熱心和真誠從事醫療事業,在很短時間內便給醫務同仁和中國病人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毫不造作的微笑,以及對他人真誠的關心,迅速贏得了大家對他的尊敬。
華理士的日常工作非常忙碌,每天一早起床,他便開始早晨的靈修,翻開聖經,選讀其中的幾頁,在心中默記經上的內容,最後低頭做一個簡短的禱告。之後他就去病房查房,察看夜班記錄,指導助手的工作。在吃早餐之前,通常先安排一個手術,如果是一般的小手術,就連做幾個。與在家鄉不同的是,現在他必須獨當一面,經常會遇到以前從未見過的病例,需要處理許多以前他未曾處理過的難題。他給病人摘除過體積龐大的腫瘤,做過極其精細的眼科手術,縫合兔唇、齶裂等手術更是家常便飯;還有闌尾切除、截肢、婦科難產手術等等。華理士用他的手術刀救治了無數的病患,在醫治患者身體的同時,也關心他們的心靈。雖然他的粵語還不流利,但關懷體貼不一定非要靠語言來表達。華理士常常向病人和他們的家屬講述耶穌基督的救恩,他懷著同情和憐憫的心,告訴他們,主耶穌愛世上每一個人。“華醫生”的名聲迅即在廣西當地傳開,許多病人慕名遠道來思達醫院專門找他求診。許多在梧州的人說:“我們在他以前聽過很多講道,但是通過華醫生和他所做的,是將其活了出來,我們看見了信仰的真諦。”3自從華理士到來後,思達醫院的病人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醫院員工靈性也得到復興。許多人得救歸主,其中有兩個家庭是全家得救,一些醫生也加入了教會。當時有兩位華人醫生公開受浸,認信耶穌基督為救主,這在當地並非易事。因為他們必須要打破本地千百年來拜偶像的傳統惡俗,承受來自家庭和社會各方的巨大壓力,但這也體現出神的權能。宣教士在梧州佈道多年,基督教會在當地也已經建立多年,許多與宣教士一起工作的華人,不是沒有機會聽聞福音,但他們從華醫生的身上,真切地看到了基督徒應有的樣式。華理士雖然訥於言辭,粵語也說得很蹩腳,不能滔滔不絕地當眾講道,但他的行為卻起到了主耶穌所說的“光與鹽”的作用,無愧於他作為一名宣教醫生的神聖職責。忙碌的工作對於華理士來說,是一件令他興奮的事。每當看到病人痊癒,他就感受到被主所用的喜樂,享受到聖經所說的“福杯滿溢”的感覺。
華理士在梧州的時期,正是日軍侵略中國之時,梧州城經常遭到日軍飛機的轟炸,很多時候華理士的手術是在轟炸中完成的。一次手術進行到尾聲時,突然遇到日軍飛機的轟炸,轉移病人已經來不及了。華理士果斷命令所有人立刻離開去防空洞避難,由他一人結束手術。中國醫生和護士離開後,華理士獨自完成手術後的所有收尾工作,隨即把病人推到一間沒有窗玻璃的大房間。這時病人清醒過來,被身邊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嚇得魂飛魄散,華理士伏下身把他按在床上,用自己不太流利的粵語盡力安慰他。日本軍機飛走後,醫護人員立即從地下室沖出來,飛跑到剛剛落下炸彈的頂樓。他們驚喜地看到,華醫生和剛剛做完手術的病人正在房間裡一起禱告。
在畢濟時院長去支援桂林的浸信會醫院時,華理士擔負起思達醫院院長的職務。1944年,梧州被日軍佔領前,醫院不得不疏散。醫院55位醫護人員停工,將醫院所有物資都轉移到駁船上,成為了一間“走動的醫院”。在華理士領導下的思達醫院,在戰火中先後輾轉藤縣、桂平、百色、南寧等地,歷時長達一年之久,經受了無數難以想像的困苦艱險和生死試煉。一位信徒對華理士說:“我們就像當年摩西率領以色列民出埃及過紅海後在曠野跋涉一樣,白天有雲柱,夜間有火柱。”4在疏散途中,他們面對嚴重的食物短缺,華理士反復鼓勵大家要沉著鎮定,藉著禱告安穩眾人軟弱的心。同時,他也費盡心思四處尋找糧食,按各人所需進行定量配給,並對患病的同工給予特別照顧。一位護士後來憶述:“有一天華醫生又把自己的那份米飯讓給了生病發燒的護士吃。飯後我走出來,沒想到無意中卻發現他躲在帳篷後面,正偷偷地把燒糊扔掉的飯焦撿回來塞進嘴裡。他看見我後,頓時顯得很不自然。我相信,平常習慣吃牛奶麵包的華醫生並不是因為吃飯焦而難為情,他是不想讓人知道他其實餓得有多厲害。他瘦得像根禾杆,看上去一陣大風都可以將他刮跑。”5奇妙的是,華理士沒有因長期饑餓和日夜操勞而倒下,反而時刻展現出一種令人佩服的非凡毅力和堅定信心。他千方百計地想辦法給大家補充營養,例如找來一些禽鳥的骨頭搗爛煮著吃,說這有利於增加維生素。思達醫院的許多醫護人員就靠這樣的方法維持生命,度過疏散轉移過程中最危險的難關。
三、為愛失去良伴
1940年,華理士第一次回國休假期間,在一次浸信會例會上遇見了一位秀外慧中的年輕女子,她是浸信會差會總部的一名職員。早在1935年華理士來總部接受差遣時,她就見過他了,並且對這個藍眼睛的瘦高靦腆的小夥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更巧的是,女孩的父母曾經在中國宣教,她本人就是在中國出生的。這因緣一下子就把兩人的距離拉近了。會上他們常常坐在一起,親切愉快地互相攀談。華理士一反平常寡言少語的態度,把她視若知己,將自己在中國幾年的所曆所聞,以及在宣教事奉工廠中遇到的種種困惑和苦惱,都向她一一傾吐。華理士登門拜訪了這位年輕姑娘和她的父母,大家一起在家裡吃了幾頓飯,暢談各自在中國事奉的經歷。彼此的瞭解和友情都更加深了。華理士離開後,兩人開始頻繁地互通書信。華理士的休假結束前,他再次專程看望女友。他們一起漫步攀談,大部分時間是華理士一個人在說,姑娘在身旁靜靜地聽。年輕醫生所談的,依然是他在宣教事奉中的種種感受。但直到最後在火車站揮手告別的那一刻,華理士都沒有對女友說出半句求婚的話,他只是請對方給他寫信,並承諾在幾年之內會再來看她。當妹妹問起時,華理士說:“我喜歡她,也許真的應該娶她,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沒能這麼做。我想過,現在這個時候,怎麼能帶一個女孩到中國去?很不安全,那裡正在打仗啊。”6
四、不斷進取,輕看榮譽
作為一名外科醫生,華理士抓緊一切時機學習科學知識。他利用短暫回國休假的時間裝備自己,進修與外科有關的課程,除了聽課、做實驗和臨床診病之外,每天晚上他都到醫學圖書館閱讀專業刊物,直到閉館的時間。他這樣作是為了更好地服事在中國的病人。他經常告誡手下的醫護人員,醫學發展永無止境,無論哪一個醫生都不可以自滿而停止學習。1947年5月,即將結束第二次休假的華理士正在諾克斯維爾的家中收拾行裝,準備兩天后前往三藩市搭乘開往中國的海輪,忽然接到一位元好友的電話:“威廉,告訴你一個好消息。你已經獲選為國際外科學會(International College of Surgeons)的會員了。”7華理士聽了大感詫異。他在中國工廠事奉了十二年,一直在梧州思達醫院默默無聞地埋頭工作,雖然親手醫治過數以萬計的病人,但從來沒有參加過什麼國際學術會議,也沒有發表過什麼醫學論著,怎麼會有機會獲得這麼高的學術榮譽呢?想當年,他謝絕父親的老朋友誠意邀請,放棄加入醫務所的難得機會,義無反顧地奔赴萬里之外的中國福音工廠,就已經沒有在學術界出人頭地的任何念頭和打算了。正因為華理士用自己的方法所做成功的臨床手術的數量,是許多美國的同行無法相比的。他完全配得這份榮譽。但華理士並沒有太多的歡喜,相反,他更加謙卑在神的面前,在滿懷感恩的同時,更加迫切地意識到神呼召他的使命尚未完成,要“趁著白晝,趕快作工。”他從沒向任何人提起這件事,直到梧州的某位同工有一天偶然意外地發現此事,大家才驚喜地知道,身處中國西南一隅、還不到40歲的華醫生,其精湛的醫術已經獲得國際醫學界的公認,達到了國際級的高水準。雖然他的醫術廣受讚譽,但他從沒有忘記自己是一名擔負大使命的宣教醫生,他的職責不僅僅是治療人們身體的疾病,更要傳揚耶穌基督的救恩,讓人認識這位元救贖萬民的全能者。回到中國後,他把診症、開藥、做手術,都看作是傳福音的機會。除了醫療治病,他也常常組織宣教隊伍到周圍鄉村去進行醫療旅行佈道。
五、深得民眾喜愛
抗日戰爭後的思達醫院,是一片頹敗荒廢的景象。華理士院長看到周圍都是病人,需要醫院。在他身先士卒的帶領下,思達醫院的修復和重建工作逐步恢復。短短一星期後,在醫院五樓彈痕累累的小禮拜堂內,全體同工舉行了莊嚴隆重的崇拜,眾人在神面前再次堅定自己奉獻的心志。禮拜結束後,大家一起下樓,來到前院,打開醫院的大鐵門。被迫關閉整整一年的浸信會梧州思達醫院正式宣告重開。
1948年夏天,梧州爆發流行性副傷寒,日夜接觸病人的華理士也不幸感染了病菌。開始時他還能向其他醫生發出醫囑,但後來病情逐漸惡化,持續高燒導致他神志不清。思達醫院的華人醫生們心急如焚,竭盡全力施行搶救。陷入昏睡中的華理士不時發出囈語,如果高燒一直這樣持續,後果不堪設想,但該用的藥物都已經用上了。傷寒是致命的傳染病,此時,醫生們似乎已經束手無策了,唯有仰望神的大能之手施恩拯救。醫院樓下的院子裡聚集著一大群人,靜靜地站在醫院大樓前面。他們當中有做買賣的、幹苦力的、討飯的、當小職員的;有基督徒、也有未信主的,全都通宵達旦一直守候在那裡。自從華醫生病倒的消息傳開後,每天都有大批梧州民眾來到思達醫院探望。由於華理士被隔離在傳染病房,他們無法親眼見到敬愛的華醫生,便日夜守候在住院部的大門前,焦急地等候著院方報告華醫生的最新病情。各地教會的信徒都在牧師和傳道人的帶領下,和思達醫院的全體同工一起,同心合意地為他們所愛的華醫生懇切祈禱。兩位美國醫生專程從廣州乘汽船趕到梧州參加會診,但除了給病人輸血和輸液之外,他們也沒有其他辦法可想。守候在醫院大樓前的群眾越來越多,雖然沒有聽到華醫生病情好轉的報告,但只要華醫生還有一口氣,大家就仍然堅持守候著,仍然抱著希望。終於幾天後,他的體溫開始下降,當醫生過來仔細探過華理士的前額和雙手後,高興地證實他的燒退了,挺過來了。喜訊立刻傳到樓下等候的民眾,人群中頓時響起了一片熱烈的歡呼聲——華醫生有救了!
六、為主殉道
抗日戰爭結束後,平靜安穩的日子並沒有持續多久,國共內戰便全面爆發。到1949年開春,時局日漸緊張。梧州的宣教士們接到在廣州的美國領事館發出的通知,建議所有美國人儘快離開華南地區。華理士和女傳道古姑娘(Miss Jessie Green)、護士長希姑娘(Miss Everley Hayes)決定留下來。他們深信,在戰亂的苦難當中,民眾更需要來自耶穌基督的平安資訊,也需要教會開設的醫療救助服務。隨著新政權對教會事工的限制越來越嚴,許多福音佈道工作已經無法繼續,女傳道古姑娘在中國信徒的勸說下決定離開。這樣,只剩下華理士和希姑娘兩人留在梧州。1950年12月19日子夜時分,一群解放軍士兵闖進思達醫院,將包括華理士在內的全體醫護人員和職工驅趕到醫院的一個大房間裡。聲稱思達醫院是一個特務窩點,而華理士就是美國總統杜魯門派遣到華南地區的間諜頭目。華理士面對指控平靜地開口說:“我們沒有偽裝什麼。我們本來就是醫生、護士、職員,奉耶穌基督的名在這裡救治病人,並沒有其他的目的。”8 但他們聲稱有證據,誣陷他藏有槍支,以間諜罪逮捕了華理士。
華理士27歲來到中國,十多年來一直以宣教醫生的身份在梧州思達醫院服務當地的百姓,雖然多次經歷戰亂和災荒中的各種危難險境,但被當局作為囚犯監禁,卻是他平生第一次。他的中國同工們也沒有想到,這竟是一場生死試煉。除了審訊者,沒有人清楚華理士近兩個月來在獄中的真實處境,因為當局不准任何人去監獄探望他。據曾經與華理士一起被囚禁而後來獲釋的天主教傳教士事後透露,在關押期間,他們見到華理士每天從早到晚所面對的,就是不停的審問、指控、逼供、和批鬥,受盡無休止的威嚇、謾駡和侮辱。他被洗腦、被要求認罪,他嘗試為每一次的審問準備自己,但審問卻一次比一次更加嚴苛,他有時甚至痛苦萬分到大哭。肉體和精神的雙重折磨,令華理士的身心飽受摧殘。他只剩下他的信仰可以堅守著。毫無疑問,他的內心經歷著極大的痛苦爭戰。同監的人有時聽到華理士在深夜高聲呼喊,有時又聽到他不斷地用力捶打牢房的牆壁。每當這個時候,就見到看守怒氣衝衝地跑過來,隔著牢房的鐵欄拿木棍猛捅華理士的身軀,直到他失去知覺。華理士在牢獄中被迫害51天后身亡。死後當局硬說華理士是自殺,讓同監牢的兩位外國神父看華理士吊在房梁上僵硬的遺體,並要求這兩位外國神父在證明華理士自縊身亡的文件上簽名。但他們不肯寫這樣的證詞,因為並沒有親眼目睹華理士自殺。經過一番爭執,最後他們只同意在一份說明在現場所見情況的檔上簽了字。當局也不准思達醫院的醫護人員進入死者“自殺”的現場,更不允許驗屍。當華理士的遺體被抬出來時,工友沒有看到任何自縊致死的表面征狀,也無法看出是否有繩索的勒痕。在更衣時,卻發現華理士的上身滿布瘀傷。看守們把華理士的遺體放進一個簡陋的木棺,隨即用鐵釘把棺蓋釘嚴封死。在幾個士兵的嚴密看護下,思達醫院的幾名同工把棺槨抬上一艘小船,順流而下到達西江邊一座小山崗上的墓園內。一個墓穴已經挖好。由於不准舉行教會的安息告別禮,同工們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禱,送別他們親愛的華醫生。沒過多久,梧州的基督徒冒著極大的風險,自發為他們所敬重的華醫生修建了一塊石碑,碑身上莊重地刻著腓立比書第一章第二十一節的一句經文﹕“我活著就是基督。” 從遙遠的美國來到梧州思達醫院事奉的華醫生,效法了主耶穌基督的樣式,畢生為主而活,並為主把自己的生命獻上,成為了活祭。
華理士自從奉差遣到梧州思達醫院擔任宣教醫生後,16年間僅回過家鄉兩次。他沒有結婚,沒有兒女。但他的事蹟傳遍美國各地和各教會,各種紀念活動持續不斷,華理士的精神激勵了無數後人去承繼他為之獻身的福音事工。
腳注
- Jesse C. Fletcher, Bill Wallace of China, 1963, p.3-4
- Ibid, p.11
- Ibid, p.29
- Ibid, p.90
- Ibid, p.96
- Ibid, p.71
- Ibid, p.107
- Ibid, p.145
資料來源
- Jesse C. Fletcher, Bill Wallace of China. (Nashville, TN: Broadman) 1963.
- “中國的華醫生”,載《生命季刊》第55、56、57、58、59期;2010年9月、12月、2011年3月、6月、9月。
- 裴斐,“華理士是誰呢?”載《臺灣浸信會神學院院訊》,第166期,2007/9/27。
關於作者
作者係美國加州基督工人神學院教牧碩士班學生,在李亞丁博士指導下撰寫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