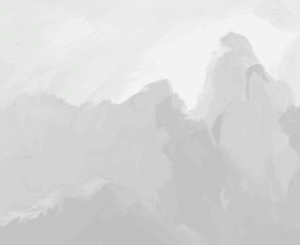理雅各(James Legge),英國倫敦宣道會宣教士,馬六甲/香港英華書院院長,近代英國著名漢學家。他是第一個系統研究、翻譯中國古代經典的人,從1861年到1886年的25年間,將《四書》、《五經》等中國主要典籍全部譯出,共計28卷。其多卷本《中國經典》、《法顯行傳》、《中國的宗教:儒教、道教與基督教的對比》和《中國編年史》等著作在西方漢學界占有重要地位。他與法國學者顧賽芬(Couvreur,Seraphin)、德國學者衛禮賢(Richaid Wilhelm)並稱漢籍歐譯三大師,也是儒蓮翻譯獎的首位獲得者。
在中國近代史上,有一批來自西方的基督教宣教士,在向中國人傳揚基督福音,介紹與引進西方先進科技之同時,自己亦為中國文化思想所吸引,最終成為著名的漢學家,以及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橋梁。十九世紀英國宣教士理雅各即是其中傑出的代表。
一、早年生活
理雅各於1815年12月20日出生在蘇格蘭阿伯丁郡亨得利鎮(Huntly, Aberdeenshire)一個富裕家庭,父親是布商。在家裏7個孩子中,理雅各最小。亨得利雖然是一小鎮,卻出了兩位偉大的宣教士,一位是首位來華宣教士馬禮遜的助手米憐博士;另一位就是理雅各。
理雅各年幼時就讀於當地的教區學校,從小就喜歡讀書,尤愛文學。14歲時轉入阿伯丁文法學校(Aberdeen Grammar School)學習拉丁文和英語語法。1831年考入阿伯丁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大學三年級時,他又醉心於哲學與宗教。在大學求學的四年中,其功課一直名列前茅。1835年,19歲的理雅各以全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畢業後,因其堅持非國教信仰而放棄了繼續在國王學院深造的機會,而接受了英格蘭布萊克本(Blackburn, England)一所公理會學校的聘請,擔任該校校長。
早在理雅各年少時,由於其家庭與在馬六甲宣教的米憐博士(William Milne)經常通信來往,加之理雅各與米憐之子美魏茶(William Charles Milne)是同學,因此他深受影響,大學時就立志做一個宣教士,獻身海外宣教事業。1837年,理雅各辭去校長職務,進入海伯利神學院(High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攻讀神學;1838年向倫敦宣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提出申請,要求前往中國宣教。倫敦會接受了他的申請,於是他到倫敦大學,師從中文教授修德學習漢語。同年,23歲的理雅各與倫敦會理事會成員約翰•摩里遜的女兒瑪麗•伊莎貝拉•摩里遜(Mary Isabella Morison)結婚。1839年7月,理雅各接受倫敦會差派,偕新婚夫人瑪麗,與米憐之子美魏茶一起從英國乘船出發,於1840年1月10日抵達南洋馬六甲。
二、馬六甲時期
理雅各夫婦到達馬六甲後,一直水土不服,健康欠佳。起初,理雅各擔任倫敦聖教書會的記者與顧問,同時在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任職。英華書院為倫敦會宣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和米憐所創辦,旨在“培養歐洲的、本地的和恒河以東國家的宣教士。” 書院校舍於1820年建成,是年秋天正式開學,米憐擔任第一任院長。
在英華書院初期,理雅各編寫了《英、漢及馬來語詞典》,用作英華書院的教材。同時他開始了漢學研究,並從事基督教漢語文獻方面的整理、翻譯與編撰工作。當馬六甲流行霍亂之時,理雅各寫了《致馬六甲華人有關霍亂書》,在當地華人中散發,從醫學角度規勸人們放棄迷信,皈信基督教真信仰。此時華人基督徒何進善(何福堂,中國教會史上第二位牧師,首位是梁發)成了理雅各的宣教助手。1840年11月,英華書院院長伊雲士(John Evans)死於霍亂,25歲的理雅各正式接任英華書院院長。1841年7月13日理雅各因“為基督教世界與文學領域的顯赫貢獻以及虔誠的信仰”而獲得美國紐約大學所授予的神學名譽博士學位。
三、香港歲月
鴉片戰爭結束後,理雅各於1843年將英華書院和中文印刷所遷至香港,自己也隨之遷居香港薄扶林,成為香港英華書院首任院長。此時英華書院的辦學宗旨也悄然改變,由一所專門培養宣教士的書院變為招收中國青少年入學的教會學校。理雅各除負責校務外,還直接從事宣教活動。他從馬六甲帶來的幾個基督徒,就成為香港的基本信眾,何進善繼續配合他設堂傳道。1844年,英華書院更名為“英華神學院”;同年理雅各在香港建立了倫敦會第一所華人禮拜堂“下市場堂”。雖然該教堂由理雅各主持,但實際上許多具體事務由何進善負責。何進善還協助他編寫、印刷漢語的福音小冊子,並將理雅各撰寫的《耶穌山上垂訓》翻譯成中文並加以註釋。1845年,理雅各籌建的佑寧堂(Union Church Hong Kong)落成;1849年他被任命為該堂的牧師。到1870年時,他已先後建立起四座教堂,經他受洗的人數達272人。
1845年11月,理雅各因多次長時間高燒不退而不得不回國治療,同時他將吳文秀、李金麟和宋佛儉三位學生帶去英國留學。1846-1848年間,理雅各巡遊英倫各地講道、演說,並向國務大臣格萊斯通報告了香港宣教近況,以及對發展教育的設想。
從1847年7月,理雅各開始參與《聖經》修訂工作,很快就卷入了曠日持久的譯名之爭。理雅各認為“神”是翻譯“Elohim”與“Theos”的合適字眼。但後來他改變了自己在“術語之爭”中的立場,選擇了“上帝”一詞來翻譯基督教的“God”。
1848年4月,理雅各與家人乘船啟程返回香港,於7月下旬抵港後,即開始與香港和廣州的宣教士籌建宣教站。不久,他的第四個女兒安妮不幸去世,令理氏夫婦悲痛不已。1850年,理雅各夫人瑪麗寫信給倫敦會東方委員會,要求對英華書院附屬女子學校予以更大的支持。該校是英華書院遷港之初理雅各授意瑪麗創建的,成為中國最早的女學之一。
1852年,理雅各在香港出版了《中國人的鬼神觀》,這是他研究中國宗教學術的真正開始。同年理雅各還撰寫了宗教書冊《約瑟紀略》、《養心神詩》(後改名《宗主詩章》)與《重修禮拜堂仁濟醫館祈禱上帝祝文》。這一年,理雅各也經歷了接二連三的打擊——10月17日,夫人瑪麗在香港染病去世,其後兩個女兒又先後夭折。1853年,他最小的女兒也死在回蘇格蘭途中。當時只留下他一個人在香港,其悲苦可想而知。但他並沒有被擊倒,在其學生黃勝的協助下,他於1853年創刊香港第一份中文報刊《遐邇貫珍》,其後他又撰寫出《勸崇聖書》、《新約全書註釋》與《耶穌門徒信經》等福音小冊子,並開始著手翻譯中國經書《周易》。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大約在1853年前後,理雅各還幫助太平天國確立了“拜上帝會”的名稱。1854年,韓山文(Theodora Hamberg)把在逃的洪仁玕帶來見理雅各,理雅各幫助安排他去教書。1855-1858年,洪仁玕成為倫敦會牧師,並作為理雅各的助理,四處講經傳道。1858年,理雅各回英國病休時,洪仁玕得湛約翰(John Chalmers)牧師資助盤纏而去到南京,做了太平天國的幹王。後來他與理雅各通信頻繁,理雅各希望他能夠糾正太平天國在信仰上的偏差,並堅持與外國人和解的路線。洪仁玕也曾托人送錢給理雅各,卻被理雅各堅辭不受。
1856年,由於人手不足和經費問題,在香港維持了13年之久的英華神學院停辦。理雅各繼續用英語和漢語從事布道與寫作。也就是在這一年,他為車金光施洗,這位車金光後來因堅持基督教信仰而被官府逮捕,旋被處死,成為中國基督徒(基督教新教)首位殉道者。同樣在這一年,理雅各英華書院的學生梁柱臣離開香港到澳洲維多利亞省建立教會。他先後在澳洲建立了三所教堂,並於1866年在廣東佛山建立起一所基督教堂,這是中國基督徒自發並自籌資金所建立的第一個禮拜堂。
1857年,理雅各因健康問題,以及為了中國經書譯著的出版事宜,第二次返英。1858年在英格蘭,通過其長兄喬治(George Legge)的介紹與安排,理雅各結識了寡婦漢娜(Hannah Mary Legge)並與之結婚。漢娜之亡夫也是位牧師,他們已有一個女兒。同年理雅各偕漢娜及其女兒和他原來的兩個女兒一起回到香港。理雅各的兩個女兒後來都在香港結婚並定居下來,分別在理雅各所建立的不同學校裏任教。
1860年,理雅各成為香港教育局決策人物,於是便大張旗鼓地推動世俗教育。1862年2月,在港府的支持下,中央書院正式開學,標誌著香港教育事業把重點轉向了世俗教育。中央書院首任校長由史釗活(Frederick Stewart)擔任。史釗活承襲了理雅各的世俗教育主張,並付之於實踐。理雅各就此把自己從教育局繁重的文秘和管理職責中解脫出來。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廣東仇外情緒強烈。1861年,理雅各曾在廣州受到當地民眾的襲擊。1861年春,他到廣東博羅看望車金光時,再次遇襲。後來,他曾冒著生命危險前往博羅解救車金光,臨行前他對英國領事說:萬一他死了,不要動用軍艦,因為他要把清白的名聲帶回家。1862年,理雅各發表一封公開信,抗議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率領英法聯軍鎮壓太平軍的行為。
1862年,中國著名學者王韜流亡香港,開始襄助理雅各翻譯中國經書,歷時20余載。1867年2月,理雅各因健康原因暫回英國養病,翻譯中國古代經典的工作暫時中斷。不久他邀請王韜去蘇格蘭,並帶他遊歷了蘇格蘭、法國等歐洲國家。此後他和王韜在格拉斯哥潛心譯書二年之久,期間譯出《十三經》。1870年1月,理雅各與其女兒瑪麗和王韜一起返華。為了方便其譯著《中國經典》的印刷和出版,理雅各與倫敦會簽約,在佑寧堂做了三年牧師,因為佑寧堂擁有印刷業務。1861-1872年間,理雅各翻譯的《中國經典》在香港相繼出版,其中第一卷含《論語》、《大學》與《中庸》,出版於1861年;第二卷《孟子》出版於1861年;第三卷《書經》與《竹書紀年》出版於1865年;第四卷《詩經》出版於1871年;第五卷含《春秋》與《左傳》出版於1872年。
在理雅各翻譯工作上,除了當時一些宣教士如湛約瀚(John Chalmers)、麥高溫(John MacGowan)、史釗活(Frederick Stewart)、合信(Benjamin Hobson)和華人黃勝等人參加助譯工作外,中國學者王韜功不可沒。王韜原來在上海倫敦宣道會開辦的墨海書館工作,於1863年來香港擔任理雅各的助手。由於王韜的具體幫助,為理雅各解釋難懂之處,並幫他寫註釋,使他得以順利地完成英譯《中國經典》的翻譯工作。
從1843年到1873年,理雅各一生中最美好的30年都是在香港度過的,他對香港的教育、報業乃至戒煙戒賭、賑災救難等公益事業皆有不菲之貢獻。除牧會、寫書和譯書外,理雅各十分關註中國社會狀況,並熱心於公益事業。他曾聯合其他宣教士和一些商會人士一千多人簽名,上書英國政府,要求取締賭場。理雅各主持的英華書院引進了西式教育,沖擊了中國的舊式教育,他在實用化的課程設置、教材使用等方面表現出了近代化的特色,有助於培養中國奇缺的專業人才並提高人才的素質。他與華人的交遊使他們成為頗有作為的社會改革人士,如黃勝、王韜、洪仁玕,以及何進善父子等人,這些人受他的影響摒棄了惟我獨尊的天朝觀念和傳統儒學中的迂腐成分。理雅各所主編的《遐邇貫珍》,大量刊載新聞,率先刊登有償廣告以維持報紙印行的開銷,同時大量介紹西方科學技術,如此向中國輸入西方近代化理念之同時,也使香港的報業近代化。香港政府為了表彰其貢獻,特於1865年頒贈一個銀盤給他,以示嘉獎。
1873年4月,理雅各到中國北方遊歷,遊覽了長城、頤和園和天壇。他認為天壇圜丘壇是世界上沒有偶像的最神聖的場所,不禁脫靴禮拜。5月前往山東,登上泰山極頂,拜訪孔子故鄉曲阜,參觀了孔廟和孔林,並拜謁了孔子墓。然後取道大運河返回上海,經日本、美國,返回英國。此番遊歷中,他也看到許多地區的落後狀況,特別看到山東孔府種植鴉片的情形,使他尤感痛心。這是一次告別之旅,此後,理雅各再也沒有踏上中國的土地,但他的“中國情”卻絲毫沒有減退。
四、牛津生涯及其歷史地位與貢獻
理雅各於1873年離開香港返回英國後,極力主張加強對中國的研究,特別是對中國文化思想的支柱儒家思想和典籍的研究。當時在英國的一些原來在中國當過外交官或經過商的英國人,如英國前駐華公使阿禮國(Rutherford Alcock),和前香港總督德庇時(John Francis Davis)等人,提出應在牛津大學設立漢學講座,並推薦理雅各為該講座的首任漢學教授。阿禮國等人又多方奔走,募得三千英鎊之巨款,專給牛津開設漢學講座之用。
1875年4月,60歲的理雅各正式應聘成為牛津大學首任漢學教授。次年,他因翻譯中國經書的成就而獲得儒蓮中國文學首屆國際獎。在1877年上海宣教士大會上,理雅各的論文“儒家與基督教之關系”(Confucianism, its relation to Christianity)由與會宣教士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代為宣讀,在西方宣教士中引起了很大的反響與爭議。
1880年,理雅各第二任妻子漢娜去世。1882年,理雅各完全失聰;1886年他又罹患中風,健康狀況惡化,但仍然堅持授課與譯述。除了繼續翻譯《東方聖書》,同時為《不列顛百科全書》撰寫條目外,他在晚年連續發表論文與出書,1879-1891年間,相繼出版了《中國古聖經典 (The Sacred Books of China)》六卷包括《書經》、《詩經(與宗教有關的部分)》、《孝經》、《易經》、《禮記》、《道德經》、《莊子》等。其他著述還有著作《基督教與儒教關於人生教義的對比》(1883年);譯作《法顯行傳》(或稱《佛國記》,A Record of Buddhistic Kingdoms,1886年加註付印);論文“菩薩的形象”(1887年);著作《基督教在中國:景教、羅馬天主教與新教》(1888年),同年將《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翻譯成英文;論文“因果報應論”(1891年)。1890年代,理雅各再次修訂了他的系列譯作《中國經典》。1893-1895年,修訂後的《中國經典》在牛津大學克萊仁登(Clarendon)出版社再版。1895年,也就在理雅各謝世的前兩年,他還翻譯出版了屈原的《離騷》。
據不完全統計,理雅各一生中著述和譯著還有:《英華通書》(Anglo Chinese calendar,1851)、《智環啟蒙塾課初步》(1856)、《聖書要說祈義》、《亞伯拉罕記略》(1857)、《往金山要訣》(1858)《聖會準繩》(1860)、《新金山善待唐客論》(1862)、《落爐不燒》、《浪子悔改》、《孔子生平及其學說》(Life and Teaching of Confucius,1867)、《孟子生平及其學說》(The Life and Teaching of Mencius,1875)、《中國的宗教:儒教、道教與基督教的對比》(The Religions of China: Confucianism and Taoism Described and Compared with Christianity,1880)、《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考》、《中國文學中的愛情故事與小說》、《中國人關於天神和鬼怪的概念》(The Notions of the Chinese Concerning God and Spirits)、《致繆勒函有關中國人稱帝與上帝》、《中國編年史》、《帝國儒學講稿四篇》(Imperial Confucianism)、《扶桑為何及在何處?是在美國嗎?》等等。
理雅各翻譯中國古代經典之工程,其結果遠遠超出其宣教範圍,對溝通東西方文化起到橋梁作用。中國儒家經典向西方的傳播,對西方的哲學思想、倫理思想、文學思想,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對此,理雅各有很大貢獻。英國漢學家Lionel Giles如此評價理雅各說:“五十余年來,英語讀者所以皆能博覽孔子之書,吾人不得不感謝理雅各君不朽之工作。” 由此可見理雅各譯著影響之深廣。
從1847年到去世,他一生半個世紀的時間都在譯介中國經書,而且是在西方人對中國人的總體歧視下進行的。他用五十余年的時間,架起了一座中西方的橋梁,他的一生是由宣教士走向漢學家的一生,他生平的活動,開始於向東方傳揚基督教信仰,然而卻顯赫於向西方傳播中國文化,至今雖逾百年,理雅各的譯本仍被認為是中國經典的標準譯本,他結束了西方學者對中國文獻業余水平的研究,走上了專業化的道路。理雅各向西方輸出的不只是中國的經典書籍,還有中國的宗教以及其他文化現象。與早期一些傲慢的西方人相比,理雅各對待中國宗教的態度是客觀、認真而尊重的,像他那樣重學術理性的宗教專著在早期宣教士中也甚為罕見。他的論述中見不到對中國無理的謾罵與攻擊,相反,他對中國文化表現出一種極為親和與尊重的態度,體現出其神學思想的開放性與獨立性。他呼籲西方人“不要在孔子的墳墓上橫沖直撞”,同時贊美中國聖賢對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對世界文化所做出的巨大貢獻。
《中國經典》的翻譯是理雅各傾註幾十年心血才得以完成一項宏大工程,他清楚意識到,只有透徹地掌握中國的經典書籍,親自考察中國聖賢所建立的道德、社會和政治生活基礎的整個思想領域,才能被認為與自己所處的地位和承擔的職責相稱。在整個翻譯過程中,理雅各始終貫徹嚴謹的治學態度,除了認真參考和吸取王韜的研究成果外,他自己也十分註重旁征博采,力求持之有據,絕不主觀臆斷。在他以前別人用拉丁、英、法、意等語種譯出的有關文字,凡能找到的,他都拿來仔細比較,認真參考,然後再反復斟酌,慎重落筆,甚至常常數易其稿。加上與王韜等人的切磋討論,就大大減少了可能有的失誤,使翻譯質量得以確保。“功夫不負有心人”,理雅各翻譯的中國經典著作質量絕佳,體系完整,直到今天還是西方世界公認的標準譯本,他本人也因此成為蜚聲世界的漢學家。
《中國經典》陸續出版後,在西方引起了轟動,歐美人士由此得以深入了解中國傳統文化,理雅各也因在翻譯上的成就與漢學研究方面的貢獻,蘇格蘭阿伯丁大學(Aberdeen University, Scotland)於1870年授予他法學博士學位;在愛丁堡大學舉行三百周年校慶慶典中,理雅各也是受到極大尊重的人物之一。理雅各在多次訪問巴黎的過程中,曾同法國著名的漢學家儒蓮(Stanislas A. Julien)進行高水平的漢學交流,並於1876年獲得法蘭西學院儒蓮漢籍國際翻譯首獎(The First International Stanislas Julie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1884年,理雅各又被愛丁堡大學授予法學博士學位。
理雅各在牛津初設漢學時,只有為數不多的學生,因為漢學在當時畢竟還是一門冷僻的學科。理雅各采取語言與文化並重的教學方法和註重翻譯的教學模式,他所做的學術報告也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中國歷史、中國文學、中國人物評傳、中國天文,以及中國社會宗教等。他在牛津大學前後共22載,培養出不少漢學家。教學之余,理雅各還花費不少時間為外國人解答漢學方面的問題。當時向他寫信求教者甚多,所涉領域甚廣;也有不少人是請他翻譯文件和翻譯刻在碗、扇等上面的文字;還有人把翻譯的稿子和研究漢字的論文寄給他審閱,為此理雅各回復了大量的信件,成為其對中國文化傳播之貢獻的一部分。
理雅各還在牛津大學開設“在華基督教傳教史”講座。他思想開放,主張西方宣教士與華人平等,甚至主張走中西宗教相互融合的道路。出於一個基督徒的良知,他對鴉片貿易深惡痛絕,認為“這是一種罪惡的交易”。在1878年倫敦舉行的一次抗議鴉片貿易的集會上,理雅各慷慨陳詞,歷數鴉片對中國人民之危害,為中國人請命。他並且引用舊約先知的話,告誡英國政府:“停止作惡,學習行善”,同時主張英國政府立法,禁止向中國傾銷鴉片。理雅各也反對英國政府介入鎮壓太平天國,或以武力介入教案。
理雅各晚年與其女兒海倫(Helen Edith Legge)相依為命,父女情深。他每天堅持寫作、翻譯和教學工作,直到力盡方休。1897年11月29日,理雅各在牛津講課時突然中風倒地,經搶救不治而與世長辭,享年82歲。學生們把他最後寫在黑板上的字拍下來,作為紀念。理雅各死後葬在牛津以北的墓地,阿伯丁花崗巖墓碑上鐫刻著“赴華傳教士與牛津大學首任漢學教授”,英國學術界為理雅各舉行了隆重的葬禮。後來,世界各地的漢學家到牛津訪問時總要到他的墓地上去獻花、憑吊。理雅各女兒海倫日後為父親寫的傳記《集宣教士和學者於一身的理雅各》(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於1905年出版問世。1928年,當東方語言大會在牛津舉行時,有來自英國、法國、荷蘭、意大利、加拿大、美國和拉脫維亞等國的漢學家,一同前往理雅各的墓地獻花,花環緞帶上寫著:“謹獻給不朽的、才華橫溢的大師理雅各。第十七屆東方學者大會全體漢學家敬獻。1928年8月31日。”
自1948年以來,根據聯合國大會的提議,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努力促成其成員國文化經典的翻譯工作,尤其是亞洲國家,但缺少能勝任的翻譯家,而且時間緊迫。最後,儒蓮編輯的《東方聖書》系列作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代表文集推出,理雅各是該系列的主要譯者之一。《東方聖書》系列在1891年由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在1966年與1968年由印度的Motilal Banarsidass再版。
在中國,1949年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註釋校正華英四書》全部采用理雅各的譯文。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湖南出版社系統出版了中國古代文獻的系列譯本,其中《四書》仍選用了理雅各的譯本。
20世紀60年代初,香港大學為紀念理雅各,再版了他的五卷《中國經典》;1961年,倫敦會捐款5000英鎊設立了理雅各獎(James Legge Prize),獎給中文系四年級本科生在畢業前用漢語或英語寫作的、對中西文化的詮釋有所貢獻的最佳論文。20世紀90年代,為紀念理雅各對香港作出的貢獻,香港政府特地在上環豎立起“理雅各博士紀念牌匾”,並於1994年10月5日發行了理雅各紀念郵票和首日封。
資料來源
- Legge, Helen Edith,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Great Britain: Religious Tracts Society, 1905.
- Norman J. Girardot, The Victorian Translation of China, James Legge's Oriental Pilgrimage.
- 王韜著,《弢園文錄外編•送西儒理雅各回國序》。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8年。
- 偉烈亞力著,《1867年以前來華基督教傳教士列傳及著作目錄》。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
- 閻振瀛著,《理雅各英譯論語之研究》。商務印書館,1971年。
- 岳峰著,《架設東西方的橋梁: 英國漢學家理雅各研究》。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2004年。
關於作者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