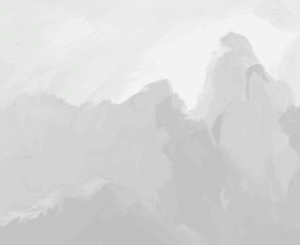一、早年生活
林樂知(Young John Allen)於1836年1月3日出生在美國喬治亞州伯爾克郡(Burke County, Georgia)。父親在他出生前兩個月去世,母親產下他兩星期後亦不幸染病身亡,幸得姨父母赫金斯(Hutchins)夫婦收養。他們都是基督徒,視小樂知如同己出,愛護有加,林樂知就這樣在充滿基督之愛的環境中長大。小學畢業後,林樂知考入牛頓郡的斯塔維爾中學讀書,在此期間接受基督教信仰,加入美國南方監理會教會。18歲時,林樂知進入愛默利學院(Emory College)讀書,於1858年畢業,獲得文學學士學位。畢業後不久,即被按立為牧師,當時年僅22歲。同年,林樂知與瑪麗•休斯頓小姐(Mary Houston)結為伉儷。瑪麗也是一才女,以優異的成績畢業於喬治亞州梅肯郡的衛斯理女子學院(Wesleyan College, Macon, Georgia)。由於二人皆有前往海外宣教之心志,故於婚後不久,他們共同接受美南監理會差會(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 Episcopal Mission)差派,前往遙遠的神秘國度——中國宣教。1859年底,林氏夫婦帶著他們新生的女嬰從紐約登船啟程前往中國,從大西洋繞道非洲好望角,橫跨印度洋路經香港,歷時210天之久,最後於1860年(咸豐十年)7月抵達上海。從此林樂知以上海為基地,開始了長達47年的宣教生涯,將其畢生的黃金歲月,毫無保留地奉獻給了中國。
二、宣教探索、文字與譯述
林樂知夫婦抵華之際正值多事之秋。在中國北方,英法聯軍攻入北京,咸豐皇帝避走熱河。在南方,太平軍席卷江南,無數百姓流離失所。林樂知原擬前往杭州開辟宣教工場,也因此被迫暫居上海。到中國後不久,他取了個中文名字叫林約翰;後取中國名言“一物不知,儒者知恥”之意,改名為林樂知,字榮章,顯示出他對中國文化的濃厚興趣。他在上海、杭州等地宣道之同時,努力學習中國文化,廣泛結交社會名流。但來華後第二年,美國南北戰爭爆發,林樂知故鄉喬治亞州加入到南方陣營。由於戰爭,監理會差會無力顧及海外宣教士的生活,這使得林樂知經費無著,不得不在宣教事工之外,兼謀一些差事來貼補家用。林樂知對這段艱苦日子曾如此記述說:“長達四年之久,我們收不到母會分文,也接不到親友片紙只字。全家生計陷入窘局,起初靠典賣教會物資暫時維持。然而此舉終非長久之計,為了養活妻兒,只能暫時擱下宣教正務,抽身出外工作賺取工錢。” 他曾先後擔任過商品推銷員,以及保險經紀人等職,以維持生計。後在馮桂芬的介紹下,林樂知在清政府辦的“廣方言館”內謀得英文教習一職;不久又應徐壽之請,到上海江南制造總局翻譯館譯書,同時還兼任字林洋行中文報紙《上海新報》的主編。據其同仁傅蘭雅(John Fryer)稱:“林氏當時工作極度緊張,晝夜不息,風雨無間。每日上午在廣方言館授課,午後赴制造局譯書,夜間編輯報紙,禮拜日則到處布道及處理教會事務。同事十年,從末見他有片刻閑暇。雖曾勸之稍稍節勞以維健康,彼竟謂體內無一懶骨。” 林樂知如此勤奮工作16年之久,根據日後《教會新報》的有關記錄,林樂知這一時期的主要譯著有《格致啟蒙博物》、《格致啟蒙化學》、《格致啟蒙天文》、《格致啟蒙地理》、《萬國史》、《歐羅巴史》、《德國史》、《俄羅斯國史》、《印度國史》、《東方交涉記》、《列國歲計政要》、《列國陸軍制》、《新聞紙》、《地學啟蒙》等10余部。1876年,清政府為表彰林樂知在譯書和教學方面的貢獻,特授予他五品頂戴官銜,後又“欽加四品銜”。同一時期,林樂知對中國社會與文化的了解也日益加深,促使他反復思考的一個問題是,如何使基督教適應中國文化,在中國得以廣傳。
在晚清時期基督教傳播過程中,大體上有兩種不同的宣教方式。一種是“直接布道式”,就是宣教士深入到中國的城市和鄉村,面對廣大的平民百姓,直接宣揚耶穌基督救贖世人的福音,散發福音書冊和聖經,以及建立教堂等。這一類宣教士較少觸及中國的社會、文化與政治問題,甚少與官紳打交道,也不從事辦報、興學、或建立醫院等事業。林樂知來華之始,采用的也是這種方法。1861年,林樂知曾與其他宣教士一道同赴南京,拜見洪仁玕等太平天國領袖,希冀從太平天國打開一個缺口,推進在華宣教事業。但由於太平天國當時忙於對付清軍的圍攻,並未對林樂知一行的宣教要求發生興趣。而另一類宣教士則采取間接的方式,註重社會關懷與服務,以愛心扶貧濟弱,以提供醫療和教育服務為主,造福人群,以引起中國人對宣教士產生好感,樂意和他們交往,進而達成傳揚基督福音的目的。1870年代之後,林樂知采取了後一種宣教方式。這種方式要求傳教士一要認真了解和研究中國社會,針對中國的文化特點去改造中國;二要把基督教義和在中國占統治地位的儒家文化相融合,再逐步以基督教文化代替儒家文化;三是以傳播西方先進的科技文化為手段,如興教育、建醫院、辦報紙等,提高中國人的素質,擴大基督教影響,以吸引更多的中國人接受基督教信仰。
林樂知以教學和譯述,將大量西方知識與科技引進中國,以影響中國人的視聽,進而對基督教產生好感。因此,林樂知對中國的社會情況極為關心,尤註重解剖晚清的社會結構。在細心觀察中國內政外交的形勢之後,林樂知得出要想使基督福音廣傳,必須抓住“士”,結交“官”的結論。他認為在中國“士為四民之首”,官和商大都來源於“士”,征服了“士”就等於征服了中國文化和社會。於是他采取“由上而下”的宣教策略,即先由上層的“官”與“士”入手,設法讓官吏士紳成為基督徒,以便達成“上行下效”,繼而向一般平民百姓傳福音,如此做法,可以收事半功倍之果效。因此他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廣交了一批“士”和“官”,如馮桂芬、李鴻章、丁日昌、張之洞等人。這些人一般思想開放,渴求新知,他們看重的是林樂知廣博的西學,而林樂知則立足於這批官紳的社會地位,試圖通過他們,自上而下,使基督福音得以廣傳。林樂知的這些交往活動使他成了當時上海地區官僚和社會名流的好朋友。
林樂知還十分注重用儒家學說來闡釋基督教教義,他將儒家的“三綱五常”與基督教義一一印證,認定二者情理相通,本質無異。他引經據典,從基督教教義中找出了論證君臣、父子、夫婦乃至兄弟、朋友的教訓,結論是:“儒教之所重者五倫,而基督教亦重五倫,證以《聖經》。” 他還認為,儒家講“仁”,而基督教的“愛即是仁也”;儒家講“義”,“耶和華以義為喜”;儒家講“禮”,而《聖經》要人們“以禮相讓”;儒家講“智”,《聖經》中稱“智慧之賦,貴於珍珠”;儒家講“信”,《聖經》中則有“止於信”,即“信”是最高美德。總之,在林樂知看來,孔子和耶穌相同,儒家和基督教相通。
林樂知另一策略是“由末而始”,意思是先“西學”而後“西教”,先傳播西方科技知識,讓中國社會的士大夫茅塞頓開,視野趨於廣闊,進而降服於西方新思想領域,然後逐漸引進基督教教義。林樂知倡導“以學輔教”的宣教策略,由此引發出他以“辦報”和“興學”這兩個途徑來實現他的宣教目標。
三、創辦與主編《萬國公報》
林樂知雖然將耶穌和孔子等同起來,但也看到在儒家思想教化下的中國人,乃至知識分子,在許多方面還相當愚昧、保守、落後,對現代科技文化所知甚少,“對自然的定律和哲學,以及化學、天文學等一竅不通。” 為便於傳播基督教信仰,首先須打破中國知識界的落後狀況,讓他們具有現代科學知識和現代思維觀念,以及新的價值取向。從這種理念出發,1880年代以後,林樂知便將其主要精力投入到傳播西方文化知識和改變中國知識界的知識結構與思維方式上。因此,他在上海譯書,介紹歐美的科學文化知識;辦報,傳播信息,宣揚基督教信仰和西方文化;創辦新式學堂,培養新型人才。
1868年9月,林樂知創辦了中文教會周刊《教會新報》(Church News);1874年9月,他將該期刊從第301期開始更名為《萬國公報》(The Globe Magazine)。1887年廣學會成立,決定將其作為機關報,仍由林樂知主編,於是《萬國公報》在1889年復刊,但英文名改為The Review of the Times,每月出版1期,直到1907年林樂知病逝而停辦。在晚清西方宣教士在中國發行的中文報紙中,以《萬國公報》為時最久,影響也最大。如果連它的前身《教會新報》合並計算,一共刊行了34年,其間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教會新報》6年。該報每周出刊一次,內容除了討論基督教教義、報道教會消息外,還介紹科學知識、外國史地與各國新聞,其發行量大體在1千到2千多份。為了吸引讀者,第2年出版的《教會新報》增加了清政府的上諭和一些政治、社會新聞。第113期和116期還刊出了赫德(Robert Hart)的《局外旁觀論》和威妥瑪(Thomas F. Wade)的《新議論略》。這兩篇論文都建議清廷效仿歐美,除舊革新,進行全面改革。林樂知轉載這兩篇時論,顯然是為了擴大《教會新報》的知名度,但從總的傾向看,該報以教務為主,較少過問政治。
二、前期《萬國公報》9年。林樂知意欲拓展《教會新報》的讀者範圍,希望藉傳播科學知識為媒介吸引教外人士閱讀,以收布道之果效,故於1874年把《教會新報》更名為《萬國公報》。其辦報宗旨雖仍以教務為主,但發生了很大的變化,那就是對晚清社會政治的關注和對中國各階層民眾及官吏、知識分子的有目的地施加影響。林樂知十分自信地稱《萬國公報》:“既可邀王公巨卿之賞識,並可以入名門閨秀之清鑒,且可以助大商富賈之利益,更可以佐各匠農工之取資,益人實非淺鮮,豈徒《新報》云爾哉!” 《萬國公報》問世後,篇幅與字數增多,發行量亦隨之倍增。
三、後期《萬國公報》19年。從1883-1888年,《萬國公報》曾因內部改組,亦因林樂知忙於中西書院事務無法兼顧而一度停刊。1889年復刊後的《萬國公報》已非林樂知個人所有,而成為“廣學會”的機關報,不過仍由他主編,改為月刊,出版銷量也增至4000多份。
《萬國公報》在中國晚清社會中,與上海的另一份報紙《申報》並駕齊驅,成為當代中國人了解世界、獲取信息的一個重要窗口,在當時中國知識分子中,被認為西學之寶庫,新知識之總匯,備受重視與青睞。許多尋求新知、立誌變革的中國知識精英和政治領袖人物,都從中得到靈感與啟迪。林樂知也因此獲稱為“教會報人”之美譽。臺灣京華書局在影印《萬國公報》時概括其內容稱:“至其內容宗旨,雖仍然不脫傳播基督教義,溝通教會消息,然亦負擔起推廣西學之責,於西洋科學知識,史事人物,國家現勢,均有涉及。其最足以歆動中國朝野士大夫之報導,則為中日甲午戰爭之際所刊載之中東戰紀。《萬國公報》遂引起朝野官紳之廣泛注意,一時視為新知識之重要來源。凡關民族自立,主權完整,政治改革,莫不有其更新之啟發。嗣後變法維新運動,很顯著受其鼓吹之影響。” 這一概述,大體勾勒出《萬國公報》之輪廓,也充分反映出林樂知在19世紀1880年代後宣教策略的根本變化,即以關心時事、傳播知識、更新中國文化、培植人才,以促進基督教在中國的發展。《萬國公報》在甲午戰爭之後由原來發行幾千份猛增到了1萬8千多份,成為晚清最有影響的報紙之一。
《萬國公報》之所以對晚清的中國人有較大的吸引力,一是在於其大量介紹和評論中國的時政;二是及時傳播西方的新思想、新知識。晚清的一些重大事件,如中日甲午戰爭、戍戌變法、義和團運動、清末新政、以及孫中山反清革命等,在《萬國公報》上都有較為詳細的報道和評論。甲午戰爭時期,該報及時報導了中日的戰況、世界各國的態度、清廷對外交涉和日本的外交,吸引了關心國家命運的晚清臣民。林樂知還以“美國進士”的名義寫了多種評論,如《中美關系略論》、《廣學興國說》等。他後來將在《萬國公報》發表的這些文章輯為《中東戰紀本末》,一時成為暢銷書。戍戌變法時期,《萬國公報》對改革頗有興趣,有關光緒帝和康梁維新派的報導很多,也對維新派支持甚力,還發表了大量宣教士對變法的建議和評論。義和團運動爆發後,《萬國公報》也先後發表了“山東義和拳匪論”、“京津拳匪亂事紀要”等文,反映出《萬國公報》反對義和團運動的鮮明立場,也留下了難得的寶貴史料。對清末的新政和孫中山的革命活動,《萬國公報》也不失時機地加以報道與評論。
《萬國公報》在介紹歐美的新知、新學方面則著墨更多。凡西方的物理、化學、數學、天文、地理、生物、醫學、制造、鐵路、輪舟、郵政、農業、漁業、開礦等新的理論、新的技術,林樂知都加以譯介,並配之以圖,給晚清的中國民眾以一種新鮮感。歐美的一些近代科學家,如牛頓、達爾文、哥白尼等,《萬國公報》亦刊出了他們的傳記。從普及自然科學知識來說,《萬國公報》可說是貢獻卓著。該報對西方新的社會科學知識,如西方的經濟學、貨幣理論、市場學、對外貿易、管理科學、教育制度、法學、圖書館學、政治學、議會知識等,都有如此這般的介紹與評價。歐洲剛剛興起的社會黨的活動和社會主義學說,《萬國公報》也都作了報導。該報第121期-123期連續介紹了歐洲的“安民新學”(即社會主義),並敘述了其基本主張。可以說,晚清中國人最早是通過《萬國公報》了解社會主義的。《萬國公報》實際上變成了晚清傳播西方文化的一個重要的窗口,許多尋求新知、立志變革的中國青年,從《萬國公報》得到了啟迪。康有為是《萬國公報》的忠實讀者,他的論著與思想,就吸收了《萬國公報》上的不少知識和理論;梁啟超在《時務報》發表的某些文章,亦明顯帶有《萬國公報》的影響;在其所撰的“西學書目表”中,就選錄“廣學會”出版的書籍共22種,其中被認為最佳者為李提摩太之《泰西新史攬要》與《萬國公報》。譚嗣同的《仁學》,也受到了《萬國公報》的影響。清末時的洋務派,以及維新派的領袖,均依賴《萬國公報》擷取新知,“廣學會”的領導人李提摩太和林樂知更被視為“變法、維新”的主要精神領袖。國父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也交由《萬國公報》公開發表,可見他對這份報刊的影響力深具信心。林語堂自稱透過《萬國公報》,林樂知成為他“生命中影響最大、決定命運的人物。” (見林語堂:《無所不談》,開明書店,273頁)。《萬國公報》不僅影響了當代中國人,甚至連日本天皇與其內閣官員也是《萬國公報》的熱心讀者,由上海的日本領事館長期訂購轉寄。到戊戌變法時,《萬國公報》的銷數激增至3萬8千份。
四、創辦“中西書院”
林樂知以譯述和辦報掀起中國社會對西方文化和科技知識的熱潮,不僅如此,他更意識到“辦學”對基督教在中國之傳播,以及改造中國社會與文化之重要。因此他為晚清的教育改革傾注了很多心力。例如他建議廢除科舉考試,將歐美的新學制引進中國等。他認為中國的科舉制度陳舊,不能適合現代社會需求,無法承受外交、軍事、科技、實業等方面的新的要求,如果繼續“專尚舉業,有害無利”。於是他與在華宣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李佳白(Gibert Reid)、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等人成立了中國教育會,計劃廣辦西式學堂。為要在上海籌辦“中西書院”,林樂知甚至暫時停止出版《萬國公報》達數年之久。
1881年林樂知辭去上海廣方言館教習和制造局翻譯職務,在上海法租界八仙橋創辦了“中西學堂第一分院”,當時置辦工料費由監理會承擔,書籍等費用,由募捐而來。第二年,林樂知又於虹口吳淞路開設了第二分院。為謀發展,林樂知在“西國勸捐,歷四五年”,購得吳淞路分院旁地皮35畝,合分院,共41畝,另建新校舍。落成後,兩分院一並遷入,學校正式命名為“中西書院” (The Anglo-Chinese College),他自任院監。中西書院的主校址坐落在今之昆山路基督教景靈堂對面。“景靈堂”原本名為“景林堂”,意為“景仰林樂知之堂”。中西書院建立後首次招生就有400余人,這個數字在當時教會學校中,似無出其右者,即使聖約翰書院也只不過70-80人。中西書院創立後,深受上海新興資產階級的青睞,很多官吏紳商大力捐助它,因而經費能夠自足。
中西書院分大書院及一院、二院三部分。大書院設在昆山橋,一院在八仙橋,二院在吳淞路。之所以取名“中西書院”,主要是為了迎合當時知識界和政界的文化思潮。在1894年甲午戰爭前後的20年間,“主以中學,輔以西學”,或“中體西用”、“中西並重”的呼聲甚高。作為林樂知助手和朋友的沈毓桂如此論說道:當今之世,“專尚中學固不可也,要必賴西學以輔之;專習西學亦不可也,要必賴中學以襄之。二者得兼,並行不悖,乃可以施非常之教化矣。” 林樂知身受美國文化和中國文化的雙重陶冶,他的“耶穌加孔子”的宣教策略雖僅是一種手段,但也包含了融合中西文化的因素。而且,提倡中西並重,容易為中國官僚和士人所理解,較直接取名教會學校要好得多。因而他在“中西書院規條”中開宗明義地寫道:“余擬在上海設立書院,意在中西並重,特為造就人才之舉。”“創立中西書院,專為栽培中國子弟起見,非敢希圖虛名,實求實濟。” 林樂知對中西書院的教學體制作了精心規劃,提出了完整的“三級教育體制”,即初級、中級、高級三等,使學生各得其所,循序漸進。在當時學生中,有誌學貫中西者卻很少,多半只為學習英文而來,因此常抱著厚西學而薄中學的心理。林樂知於是再三向學生們強調“中學不能精熟,西學必不能通達”,勸勉他們勿圖近功、勿逐小利,不要以畢業後進入洋務機關,如海關、輪船招商局、電報局、礦務局等為滿足,而要以將來能夠領導國家的現代化運動為抱負。
中西書院具體日常事務由沈毓桂主持。在課程設置上嚴格按中西並重的原則,一般是半天中學,半天西學。中學主要是講解古文,作詩造句,寫對聯,學書法,熟讀《五經》等。西學課程則新鮮而具體,其八年課程設置如下: 第一年 認字寫字,淺解辭句,講解淺書,習學琴韻。 第二年 講解各種淺書,練習文法,翻譯字句,習學琴韻,習學西語。 第三年 數學啟蒙,各國地圖,翻譯選編,查考文法,習學琴韻,習學西語。 第四年 代數學,講求格致,翻譯書信,習學琴韻,習學西語。 第五年 考究天文,勾股法則,平三角,弧三角,習學琴韻,習學西語。 第六年 化學,重學,微分,積分,講解性理,翻譯諸書,習學琴韻,習學西語。 第七年 航海測量,萬國公法,全體公用,翻譯作文,習學琴韻,習學西語。 第八年 富國策,天文測量,地學,金石類考,翻譯作文,習學琴韻,習學西語。
宗教科目在教學內容中所占的分量很少,沒有規定的聖經課,學生也無須成為基督徒。但作為一所教會學校,中西書院的學生每天早晨必須“恭讀聖經”,並作統一的祈禱儀式;星期天則要前往教堂作禮拜。在這一點上,林樂知是很開明的。1887年後,林樂知的主要精力轉向廣學會和辦報紙,對中西書院過問減少。1895年他辭去中西書院校長職務,由美國監理會另外派人主管。後任校長的宣教士一改林樂知的風格,加重了基督教課程,將書院辦成了一所地道的教會學校。
1900年,美國監理會決定合並蘇州博習書院(Buffington Institute)、宮巷中西書院(Kung Hang School,1896年)和上海中西書院,擴建為東吳大學;校址設在蘇州天賜莊。林樂知為董事長、孫樂文(David L. Anderson)為校長;東吳大學主樓被命名為“林堂”,以紀念林樂知之貢獻。1912年,中西書院正式遷往蘇州,並入東吳大學,原有校舍改為東吳大學的第二附屬中學。
中西書院否定了清廷的科舉制,傳播了美國式的教育制度,對清末民初的教育改革具有示範作用。中西書院前後歷32年,培養與造就了數以千計的、和封建傳統相對立的、具有一定西學基礎的、大體能適應近代社會的新型人才,在晚清的外交部門、海關、對外貿易、近代工廠、新式學堂、北洋海軍等地方,皆有中西書院的畢業生,這對中國由封建社會轉入近代社會意義重大。
五、創辦“中西女塾”
林樂知來中國後,親見中國女子由於沒有受教育的機會而造成社會之種種缺憾與弊端。因此他強烈反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封建觀念,熱心推動中國的女子教育。林樂知以基督教平等觀念看待中國婦女,曾發表大量的文章,論述女子教育的必然性和重要性。在他看來:“人之所以為人者,學問而已矣!無學問者不得謂之人。彼雖靦然人面,其與飛走之屬固何別也?” (林樂知“中國振興女學之亟”,載《萬國公報》1905年8月)“學問為成人之利器,無論其為男人或女人,關於身家,或關於國家,皆當以求知為先。以就中國而言,則以振興女學為最要。” (“論女學之關系”,載《萬國公報》1903年度11月);女子受教育“大而言之,固將擔任國民一分子之義務;小而言之,則亦相夫育子,謀一家之幸福而有余。夫一家之內,亦男女各半,棄女不教,使為廢物,無異自敗其國也。” “今日之振興女學,殆不能譏為一急之務矣!” (“振興女學之關系”,見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第606頁) 林樂知把女學看成是富家、強國、婦女解放的根本。
由於成功地創辦了中西書院,林樂知建議美國監理會婦女傳道部在上海開辦女學,招收上海上流社會女子。1890年監理會批準在上海設立女學,於是林樂知和美國監理會女宣教士海淑德(Laura Haygood)在上海慕爾堂(今西藏路沐恩堂)西側創辦了“中西女塾”(McTyeire, 即後來的中西女中),於1892年3月正式開學,開創了中國女子接受教育之先河。林樂知將西方婦女教育模式引進到中國來,學制10年,雖其辦學原則是“中西並重,不偏依”,實則以西學尤其是英文為主。中西女塾在教學過程中,舉凡格致、算學、地理諸科以及宗教,只要學生力所能及,皆以英語教學,與中西書院不同的是宗教課是必修課程之一。中西女塾開辦時僅有學生5人,但隨著風氣漸開,學生日益增多,而且學生多來自上海的富有家庭,中西女塾也逐漸成為當時上流社會富裕家庭女兒出外留學前,先行接受英語教育的殿堂,以致有“貴族學校”之稱。對中國近代史影響重大的“宋氏三姐妹”,趙元任夫人楊步偉女士等,皆曾先後就讀於中西女塾。到20世紀,該校更為中國培養出不少女性人才。
六、對中國婦女解放之貢獻
林樂知和當時許多西方宣教士一樣,最感到困惑的便是中國婦女纏足之風俗。按照基督教觀念,婦女纏足是“負上帝造人之本真” (“纏足論衍義”,載《萬國公報》1889年4月),也就是說這種蓄意摧殘人的肉體與靈魂的行為,是破壞了上帝造人的意願。在基督教信仰中,世間男女,無論他們人生處境如何,均在上帝面前一律平等。林樂知在《萬國公報》上發表大量言論,反對中國人對婦女身心健康的摧殘,表現出一個基督教徒所具有的憐憫之心與救世情懷。“以布條緊紮,使其肉糜骨折,痛楚難堪,致生成之善足,變為殘跛之廢人,畢生艱難,趨步不便,欲求其小,不顧其苦,貪其美,不計其害。” “皮肉潰爛,疼痛號泣,艱地步履,忍受終身之苦厄。” “觀纏足之時,緊紮呼痛,母即酷打其女,強使之痛楚難堪,旁觀之人,每為傷心,其父母反鐵石心腸,絕無惻隱。嗚呼!殘忍若是。” (抱拙子:“勸戒纏足”,載《萬國公報》1882年10月)。同時,林樂知看到纏足實際上是一種在腐朽文化支配下,對廣大婦女施加的刑法,其醜陋程度超過世界任何國家風俗中對人性的摧殘。讓他無法忍受的是,中國人居然把這種毀壞人性的惡劣行為,卻視為是一種趨之若鶩競相贊嘆的“美”。在其“裹足論”一文中,他直斥其謬:如果一個女人,她哪怕是三寸金蓮,“而縮頸粗腰,安望其步履珊珊耶?美者,不因乎裹足而愈美;醜者,不因乎裹足而不醜。”(《萬國公報》1878年8月)
纏足不僅危害人的心靈與健康,而且還對整個民族的血脈相傳產生消極影響。林樂知深感此害,從遺傳學角度說明這種毒害民族的醜惡行為:纏足勢必造成婦女身體的衰弱,身體的衰弱就會造成身體發育的障礙,這樣生下的孩子就可能身體單薄,智力低下。此外婦女由於身體的殘疾,會對性格造成重大影響,最明顯的是膽小怯弱,這勢必又影響到孩子身上。中國之衰落,婦女的纏足之害難辭其咎。由於婦女纏足,使中國一半人口變成殘廢,這樣的國家焉有不弱之理?故而纏足是“違天意、蔑古制、招痼疾、戕生命、妨生計、廢人倫和壞心術。”(“纏足兩說”,載《萬國公報》1895年5月)。而今日之中國要強大起來,必須要改造人,使人具有強健的體魄,做到這一點就必先除去像纏足一樣的各種惡俗,鏟除對人性的壓抑與摧殘,按照自由平等之理來重建中國人的價值觀念。
纏足既然對個人、家庭、國家都造成如此巨大之危害,那麽怎樣才能革除此弊呢?林樂知等宣教士認為“病根甚烈且久,非用猛法以治之”不可。他們仗義執言:首先是政府要以行政手段強制廢除纏足之俗,官員在這方面要起帶頭作用,譬如三品以上官員所生女兒,不得纏足,否則治其有罪。其次用各種方法向中國人宣傳此等惡俗之醜陋,逐漸廢除此俗。第三是采用經濟制裁手段,“按戶按口,遍量其足,凡小三寸者,日捐錢30文;足大至5寸半,日捐僅錢5文;若至6寸即可免捐。纏更小者照數加捐,放略大者照數減捐。若竟有小逾3寸者,則加捐至日50文。”(“天足會陳詞”,見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第855頁)
為了扭轉中國人對婦女的態度,以改變中國婦女的地位,林樂知在中國基督徒任廷旭的協助下完成了洋洋21冊的《全球五大洲女俗通考》(Women in all Lands)一書,於1903開始陸續出版。該書以婦女地位的高低為文明興衰的指針,對各國文化進行比較和研究。除文字之外,還附有圖片一千余幅以吸引讀者。根據“廣學會”成立40周年時(1927年)的統計報告,在其最暢銷的書籍中,此書高居第二位。林樂知寫這部書的目的是以“各國女人之地位,與其看待女人之法”來考查中國對待女人的態度,以及在各國之中,居於何等地位。他一再強調一個國家的婦女不解放,絕無振興之望,這對貧弱的中國來說更是如此。“所謂釋放女人者何也?釋放世人,固為第一要務;但釋放女人上端,實為拯救東方諸國之良法,而中國尤亟,因對癥發藥,非此不能奏效也。” (“論中國變法之本務”,載《萬國公報》1902年6月) 林樂知反復告誡中國人,婦女的地位和國家強弱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以此喚起人們對婦女解放的重視。
林樂知和西方宣教士在中國婦女解放上的所作所為,沖擊了封建觀念,啟迪、刺激了中國人的思想。康有為反對婦女纏足的思想與行動,就是受到《萬國公報》上文章的啟發,從而於1883年在家鄉南海縣成立了“不纏足會”,成為中國人自己創辦的第一個不纏足會。梁啟超在外國宣教士興辦的女學面前,感到“俟教於人”的恥辱,於是在上海聯合同仁,創辦了第一所女學。如果當初沒有這些西方宣教士的努力,中國的婦女解放運動無疑將會推遲幾十年。從這方面來說,正是林樂知這些人使中國婦女在萬馬齊喑的黑暗社會,看到了一絲曙光。因此,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有林樂知等西方宣教士的巨大貢獻。可以說,他們是率先引導中國人脫離愚昧無知的思想導師,更是推動中國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
七、文字出版與著作
林樂知還和韋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和丁韙良等人組織成立了基督教文字出版機構“廣學會”,出版發行基督教信仰與文化圖書,以擴大基督教在中國的影響。林樂知在其“廣學興國說”一文中解釋道:“會以廣學名,廣西國之學於中國也。中國自有學,且自有至善之學,斷不敢勸其舍中而從西也。” 到1890年代,因廣學會和《萬國公報》的工作越來越吸引林樂知的興趣,遂於1895年辭去中西書院院監的職務,專事辦報與譯著。在中國數十年間,林樂知兼教習、作家、翻譯家、編輯和宣教士於一身,通常是半天授課,半天譯書,夜間編輯期刊,禮拜天傳道。其譯著有十多種,最為著名的是《中東戰紀本末》初編8卷,於1896年4月出版。初版3000冊很快銷售一空。1897年又出續編4卷;1900年再出3編4卷,全書共16卷。此書不單純是翻譯,間有編者的按語、評論、對甲午戰爭真相的披露,以及對中國所存之積習與惡俗的尖銳批評。此外,林樂知還著有《文學興國策》、《新治安策》、《中國歷代度支考》、《中日朝兵禍推本窮源說》,以及《印度隸英十二益說》等書。這些書籍對中國知識界影響很大。在其《治安新策》中,林樂知總結了當時中國的八大積習:1.驕傲,自滿於固有的聲名文物;2. 愚蠢,讀書人旅行者少,即使受過教育的儒生,也不明世界大勢及天文、地理、物產方面的常識;3. 膽怯,不思進取,亦不敢冒險;4. 欺誑,官樣文章、欺上瞞下;5. 暴虐,濫用刑罰、草菅人命;6. 貪私,人各顧己,不顧國家,官吏盤剝百姓,將校克扣軍餉;7. 因循,拘守舊章,不因時變通;8. 遊惰,空費光陰,虛度日月(顧為民《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第234頁)。林樂知所見入木三分,反觀一百多年後之中國,這些積習仍在,尤其是第3-8條,幾乎全盤繼承下來,值得國人深思與反省。
由於林樂知在中國所做的巨大貢獻,當他於1906年5月短期回國的時候,受到當時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Theodore Roosevelt)的接見,這是極高的榮譽。會面時,林樂知慎重的向總統陳明中國人對西方列強加諸於中國的不平等條約深惡痛絕,建言總統應盡快加以廢止,從中可見他對中國人的愛之深。
1906年,70歲的林樂知返回上海,正當他躊躇滿誌,計劃進一步擴展他的事業時,不料卻在1907年5月30日清晨突然病逝,享年71歲。林樂知死後備極哀榮,各方悼念文字甚多,緬懷這位信仰與文化之巨擘。林樂知將其一生都奉獻給了中國。他雖然生為美國人,但其生活在中國的年月,遠超過在其母國。在47年悠長歲月中,他在宣教、辦報、創設學校,翻譯書刊、著書立說、以及引進西方文化與科技各個方面,皆克盡厥職。他集宣教士、教育家﹑翻譯家、作家﹑報人於一身,更是中國現代化的播種者。
資料來源
- 林樂知主編,《萬國公報》,1878年8月刊;1882年10月刊;1889年4月刊;1895年5月刊;1899年11月刊;1902年6月刊;1903年11月刊;1905年8月刊。
- 梁元生著,《林樂知在華事業與萬國公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78年初版。
- 魏外揚著,《中國教會的使徒行傳》。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2006年。
- 黃昭弘著,《清末寓華西教士之政論及其影響》。宇宙光1993年初版。
- 顧為民著,《基督教與近代中國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 李又寧、張玉法編《近代中國女權運動史料1842-1911》。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5年。
- 姚崧齡著,《影響中國維新的幾個外國人》,傳記文學出版社。
關於作者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