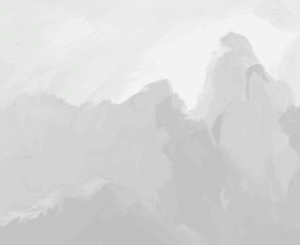自幼就讀“嚴館”
梅貽琦,字月涵,於1889年出生在天津。其父梅臣是清末秀才,後為天津鹽務局職員。梅貽琦系家中長子,下有五個弟弟和四個妹妹。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時,梅家逃往保定避難。亂定之後,一家人雖然得以返回天津,但父親卻失去了工作,從此家道中落。“除去幾間舊房庇身以外,夠得上是準無產階級了。” 但梅父沒有放棄對子女的教育,家境雖不富裕,仍堅持送孩子上學讀書。梅貽琦是天津嚴範孫家塾“嚴館”最早的學生之一。後來,“嚴館”成為一所西式學校並最終在張伯苓校長的努力下,使之變為南開學堂,繼而南開大學。梅貽琦在“嚴館”熟讀四書五經,故國學功底深厚。日後他曾對朋友說:“假如我們之中有誰背誦任何中國經典有錯漏,我可以接著背誦任何章節。” 在南開學堂,梅貽琦成為張伯苓的得意門生。
“庚款”學生留美
1908年,梅貽琦以全班第一的成績畢業於南開中學後,被保送到保定高等學堂讀書。1909年,清政府外務部決定利用美國退還的部分“庚子賠款”作為派遣留學生赴美國學習之用,因此成立了“遊美肄業館”,在北京西郊的清華園興建校園,作為預備留美學生的預科學校。校園建成後,外務部將遊美肄業館改稱為“清華學堂”。1911年4月29日,清華學堂開學,這就是清華大學建校紀念日的由來。1912年清華學堂改稱為“清華學校”;1925年清華學校設立了大學部,1928年清華學校又改稱為“國立清華大學”。
1909年6月,梅貽琦考取了首批赴美留學生,在所有47人中名列第六名。因而得獲庚子賠款留美獎學金,遠赴馬薩諸塞州格羅頓的勞倫斯學校(Lawrence Academy)讀書。次年秋天,梅貽琦開始在伍斯特理工學院(Worcester Polytechnic Institute, WPI )學習電機工程。就學期間,他被選為電機俱樂部副主席。在校的最後兩年,他住在學校的世界會(Cosmopolitan Club )裏,並先後擔任世界會的秘書、財務總管和主席。此外,他還在1912至1913年期間擔任全美中國學生聯盟東部分會的英文秘書。在一次基督教青年會組織的夏令營會上,梅貽琦決志成為基督徒。此後,他積極參與校內基督教青年會和中國學生基督徒協會,並且在1913年12月作為代表出席在堪薩斯市(Kansas)舉行的全國學生志願者大會。大學畢業那年,他擔任了全美中國學生基督徒協會的財務總管。
從任教清華到教務長
梅貽琦於1914年獲得電機工程學學士學位後回國,首先到天津基督教青年會服務一年,任幹事職。翌年秋,梅貽琦受聘成為清華學堂的物理和數學教授。暑假期間,他回到天津見到張伯苓時,流露出自己對教書沒有興趣,張伯苓回答說: “你才教六個月就不想教了,你怎麽知道自已沒有興趣呢?年輕人要學會耐心。回去,繼續教下去!” 日後,梅貽琦每憶及此,便說:“這可倒好,這一忍耐,幾十年、一輩子下來了。” 1919年6月,梅貽琦和韓詠華在北京東城基督教青年會結婚,當時梅貽琦已30歲,韓詠華26歲。韓詠華是韓家聰明、漂亮的的大女兒,梅胎琦當初在天津“嚴館”讀書時,韓詠華也在那裏,只不過當時她不得不女扮男裝。三年後她考取了幼師,畢業後在兩所學校的幼兒園任教,業余時間在基督教女青年會工作。在此期間,她與梅貽琦正式相識並訂婚。自1919年結婚後,兩人共同生活了43載,生育了五個孩子。
1921年,梅貽琦再次赴美,到芝加哥大學深造。1922年獲得機械工程碩士學位,在歐洲作短期遊歷後歸國,9月回到清華繼續任教。1926年春,梅貽琦被清華教授會推舉為教務長,時年37歲,在教授中是比較年輕的。之所以選中他,乃出於大家對他人品的信任。
1928年,梅貽琦奉派前往美國華盛頓,擔任清華留美學生監督,管理清華大學在美留學生事宜。工作要求他前往各個學校檢查工作,探望、關心那些留學生。他還將自己的辦公室變成留學生的家,常常為他們舉行各種聚會和活動,遠道而來的學生就在他家裏住宿。
清華大學校長
1931年,梅貽琦接受聘請回到清華大學擔任校長,時年42歲。當時國內局勢風雨飄搖,學潮叠起,尤以北大、清華為甚,驅逐校長的運動可以說是此起彼伏。在梅貽琦赴任之前,學生們已經趕走了三位校長。在1931年12月舉行的就職典禮上,梅貽琦說:“本人能夠回到清華,當然是極高興愉快的事,可是想到責任之重大,誠恐不能勝任,所以一再請辭。無奈政府方面不能邀準,而且本人與清華已有十余年的關系,又享受到清華留學的利益,則為清華服務乃是應盡的義務。所以只得勉力去做,但求能盡自己的心力,為清華謀相當的發展,將來可告無罪於清華是矣。” 他並且引用古語表達自己對清華的熱愛:“生斯長斯,吾愛吾廬。”
梅貽琦是一個謙虛、勤謹、忠誠敬業和責任心很強的人。他個性沉靜、少言寡語、慎思熟慮,注重實幹,時人稱之為“寡言君子”,但他不乏幽默感。他自己說:“為政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其同仁葉公超則用“慢、穩、剛”三個字形容他;而清華學生則以梅貽琦的口頭禪來形容其校長的謹言慎行:“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可是不見得。” 但學生們從未攆過這位校長,無論什麽時候,清華學生們的口號都是“反對×××,擁護梅校長”。有人問梅貽琦有何秘訣,他幽默地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願意倒梅(霉)!” 梅貽琦把自己比作京戲裏叫作“王帽”的角色:“他每出場總是王冠齊整,儀仗森嚴,文武將官,前呼後擁,像煞有介事。其實會看戲的絕不注意這正中端坐的‘王帽’。他因為運氣好,搭在一個好班子裏,那麽人家對這臺戲叫好時,他亦覺得‘與有榮焉’而已。” 也許正因為此,許多名人往往是“名滿天下,謗亦隨之”,唯有梅貽琦在身後贏得“翕然稱之”,“胥無異詞”等溢美之詞。
梅貽琦出任校長後,奉行“教授治校”原則,由所有教授和副教授組成清華大學教授會,其權限包括審議、改進教學及研究事業,以及學風的方案;學生成績的審核與學位的授予;從教授中推薦各院院長和教務長。教授會由校長召集和主持,但教授會成員也可以自行建議集會。校務則採取分層負責制,既講民主,也法度嚴明。
在任職清華校長十七年裏,梅貽琦一貫提倡和推崇教育獨立與思想自由的精神。他接掌清華僅四年後,清華的學生即較前增長了一倍,由原來的600人增加到1200人。學校設置了十個研究生科系,占全國所有研究生科系的三分之一強。在人文與社會科學方面,清華僅次於北京大學,位居全國第二。梅貽琦不僅新建和擴建了化學系大樓、五個學生宿舍、餐廳、教職員住宅區,還將圓明園遺址附近的一些土地買來,讓生物系進行農業方面的試驗性工作。梅貽琦特別鼓勵中西學術交流,除不斷邀請美歐科學家來清華舉辦講座外,他還積極支持教師出國講學與在國外發表論文。梅貽琦首開先例,實行休假制度——教授工作一定年限後,就可以休假一年。若利用休假時間赴歐美從事研究,學校提供經濟支持。清華大學在他的領導下,得以在十年之間從一所有名氣但尚無學術地位的學校一躍而躋身於中國名牌大學之列。
梅貽琦管理學校的方法包括明確原則和授權委派,一旦大的方針政策得到確定,教職員工在達成既定目標的前提下擁有相當大的工作自由度。“這種真誠的信任使大家都能在工作中盡自己最大的努力。” 梅貽琦也嘗試著將中西文化中兩種不同的教育理念在清華大學結合起來。中國的教育理念是使受教者能夠“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西方人文教育則強調“平等和自由”——大學有獨立於政治的自由,教授和學生有學術和信仰自由。他相信“這兩個原則基於基督教文明,即上帝賦予人自由意志,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
在延攬人才,聘請教師方面,梅貽琦總是盡上自己最大的努力。早在他做教務長,實際主持清華國學研究院院務時,曾親自到火車站去接趙元任先生;他和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即王國維、梁啟超、陳寅恪、趙元任,一直保持著誠摯的友誼。梅貽琦的慧眼識才及求賢若渴,更在華羅庚身上得到充分的體現。華羅庚從一個只有初中學歷的人,先做小學教員,後為店員,被破格召進清華大學加以培養;又破格從一位系資料員轉升為助教,而且被允許修讀大學課程;破格被送到英國劍橋大學去“訪問研究”;最後又破格未經講師、副教授階段而被聘為教授,這整個過程大多是在梅貽琦親自過問下實現的。
對於學生,梅貽琦一貫採取愛護態度。抗戰爆發前夕,清華學生抗日情緒非常激昂。有一次,宋哲元派軍隊到清華清查,嚴令士兵們不得使用槍彈,不想竟被學生們繳了械,領隊的團長也被扣留,運輸車輛亦被掀翻。這下惹了大禍,當晚就有一個師的部隊荷槍實彈進入校園,結果有大約20學生被捕,而且大都是無辜的。次日,梅貽琦召集全校師生講話,以沉痛的語氣告誡學生:“青年人做事要有正確的判斷和考慮,盲從是可悲的。徒憑血氣之勇,是不能擔當大任的。尤其做事要有責任心。你們領頭的人不聽學校的勸告,出了事情可以規避,我做校長的不能退避的。人家逼著要學生住宿的名單,我能不給嗎? ……我只好很抱歉地給他們一份去年的名單,我告訴他們可能名字和住處不太準確。” 最後梅貽琦表示:“你們若還要逞強稱英雄的話,我很難了。不過今後如果你們能信任學校的措施與領導,我當然負責保釋所有被捕的同學,維持學術上的獨立。”
1931年,日軍占領中國東北後,清華的學生們要求政府立即對日宣戰。學校為支持學生而停課三個星期,讓學生可以參加軍訓。華北地區和華中地區的學校也紛紛採取同樣的方法支持抗日。抗戰期間,清華校園學生為抗日,為愛國,為向當局施壓,經常舉行示威遊行,甚至和警察發生激烈沖突。在這種政治動亂的情況下,梅貽琦始終努力在清華維持一個相對正常的校園學習環境,極力設法避免外界對學校生活的干擾,以致清華大學被譽為中國北方唯一可以找到“一張平靜書桌的地方。”
西南聯合大學校長
隨著日軍大舉侵華,國民黨政府決定將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遷往內地,在長沙合組成“國立長沙臨時大學”。開課僅兩個月,南京失守,華中危急。1938年,“長沙臨大”又奉命遷往雲南昆明、蒙自兩地。清華師生遂攜帶著實驗室設備和圖書,或徒步,或乘坐車船,輾轉千里,最後於1938年4月抵達昆明。清華、北大和南開三所大學聯合組成了“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簡稱“西南聯大”,由張伯苓、蔣夢麟和梅貽琦三人組成常委會,梅貽琦出任常委會主席兼校長。同年5月4日。“聯大”開始上課。那時,“西南聯大”是中國最大的學校,共有26個系,兩個訓練部門和一個預科部,共有註冊學生3000多人。是年夏天,梅夫人帶著五個孩子取道上海、香港、到昆明與丈夫團聚,開始了在”西南聯大”將近八年的生活。
當時師生的學校生活條件極差,戰時通貨膨脹,物資匱乏,教授們難以維持家庭生計,學生們每日兩餐皆為素菜白飯,以至於1943年11月的《星期六晚報》這樣描述說: “食不果腹的老師在教一群饑腸轆轆的學生。” 1938至1941年間,日軍飛機頻繁空襲昆明。白天,師生們常常要“跑警報”,即跑到莊稼地或墓地裏躲避空襲,空襲過後再回到教室上課。作為校長的梅貽琦和師生們同甘共苦,他和妻子、四女一子每天的基本食物只是辣椒拌飯,出門以步當車。為了不使教職員工和學生們挨餓,梅貽琦想方設法為大家解決生計問題,如派人到農村去採購糧食,或把學校內一些多余的設備賣掉。在那艱難的八年裏,大家公認“梅貽琦校長一心為公益”。他的簡樸、誠實與慷慨助人贏得了人們極大的尊重。
戰時因圖書、資料和設備不足,學校課程難免受到影響,但學生們也能因從三所學校的179位專家那裏選課而大大受益。除了23位教師,其余所有的正副教授全都在美國或歐洲學習過。當時主管各職能部門的負責人,無一不是飽學之士。校委會秘書長楊振聲是中國文學教授;前後兩屆教務長是社會學教授潘光旦;負責新校舍建設的建設長是教育學教授黃鈺生。清華的散文家朱自清、詩人聞一多和國學大師吳宓主導了聯大的中國文學系;此外還有一些清華的著名學者服務於聯大,包括陳達(1916屆社會學系)、梁思誠(1924屆建築設計系)、吳晗( 1934屆歷史系)等人。梅貽琦還起用那些頗有建樹的青年學者擔任教職,如陳省身和華羅庚(數學系)、周培源(物理系)、陶寶楷(工程系) 和陳岱孫(經濟學系)等。他們中許多人能夠在講課時使用英語,使用美國和英國的教材。所以盡管戰時的處境很糟,聯大在教學上始終保持著高標準。聯大的實驗室雖然曾經三次被炸,但裏面每日仍有很多充滿熱情的學生,他們中間有許多人後來成為中國科學院、北京大學和復旦大學的科學家和教授。1957年,聯大的兩位畢業生楊振寧和李政道獲得了諾貝爾物理獎,西南聯大培養、造就領袖人物的作用為世界所肯定。
由於梅貽琦多年來在清華大學卓有成效的工作,1940年,其母校,麻省伍斯特理工學院在他缺席的情況下授予他榮譽工程學博士學位。
梅貽琦憑借高超的智慧和領導能力幫助清華度過了混亂的30年代,又幫助中國最好的三所大學度過了戰亂的40年代。戰爭於1945年8月剛剛結束,新的挑戰就來到了面前。戰後第一年,梅貽琦負責重建遭日軍洗劫的清華校園,準備回遷。抗戰期間,清華校園被日本軍隊當作醫院、酒吧、妓院和養馬場。學校百分之九十的家俱和設備都丟失了,大部分校舍遭到嚴重毀壞。避亂八年後,聯大於1946年5月4日在昆明舉行了停辦儀式,那天正好是五四運動27周年紀念日。參加的人員有2000名學生和教授、校友,以及地方來賓。然後他們同無數戰爭難民一起踏上艱辛的返回北方家園的路程。1946年10月10日,清華校門重開,學生人數較戰前增加了兩倍多,其中人數增加最多的是工程系。清華還用庚子賠款基金累計的利息購買了許多圖書和設備。
教育理念
自1931年梅貽琦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後,他堅持民主辦學、學術自由的方針,以他一貫廉潔奉公、公正嚴明的作風,受到全體師生的歡迎和敬重。從擔任校長之始,他就提出了自己幾個基本的教育理念。在其就職演說中,他首先講到辦大學的目的:“辦學校,特別是辦大學,應有兩個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才。” 這一理念主導著他畢生辦學的方向與實踐,無論是在北京的清華,或在西南聯大,還是在新竹的清華,他辦學的目的都是圍繞這樣的核心理念,即研究學術與造就有用的人才。為此他始終堅持兩點,即保證學術自由和聘請學有專長的學者來校任教。為“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他推行了蔡元培先生“兼容並包”的辦學主張,因此在清華和西南聯大的校園內始終薈聚著學術思想上的各家各派。有校友回憶說:“梅校長主掌清華,始終以民主思想、學術自由的開明政策為治校原則,他對左右派的思想兼涵並容,從不幹涉。” 為造就有用之人才,他提出了著名的“大師”說:“一個大學之所以為大學,全在於有沒有好教授。孟子說:‘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我現在可以仿照說:‘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這段話成為其教育理念之名言,一直為教育界人士所稱道。此後清華大學延聘了一大批學貫中西的知名學者,一時清華教授陣容之強在國內名列前茅,他們使清華的文學院、理學院、法學院、工學院及研究院得以充實並發展。
對於青年學生的教育,梅貽琦採取了通才教育,或“自由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的模式。這是一種以中國古代儒家“大學”教育思想為基礎,博採近代中外大學教育思想的精粹融合而成的、具有獨立性的思想體系。他認為,大學階段的直接培養目標應該是“通才”,不應該也不可能負擔起直接為社會各行各業培養“專才”的任務。這種任務應該由其他教育機構來承擔,而大學應著眼於為學生們通向高深而做基本訓練。這種通才教育要求學生不僅應有專門的知識,更應受到貫穿在整個大學課程中的普通教育,使每個學生對於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皆能融會貫通。
梅貽琦的教育思想還體現在他所提倡的“五育”中,即德、智、體、美、群,這是對蔡元培教育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梅貽琦把德育作為“五育”之首,並且首先強調教師的師德,在他眼中的“大師”,是學問、道德皆優秀的楷模。他認為,教師不單要能“以己之專長之特科知識為明晰講授”,而且要為學生的“自謀修養、意志鍛煉和情緒裁節”樹立楷模。為此,他提出了“從遊”這一生動的比喻,以老師為大魚,學生為小魚。認為“學校猶水也,師生猶魚也,其行動猶遊泳也。大魚前導,小魚尾隨,是從遊也。從遊既久,其濡染觀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為而成。” 此即為著名的“從遊論”,即以教師的高尚品行來自然地引導學生,達到“不為而成”的教育方法。其次,梅貽琦認為大學應該注重對學生“人格”的全面培養,至少應該有知、情、志三個方面。
梅貽琦亦深知惟有具備健康的體魄,才能完成學業,才能在將來成為有用之才,而且能發展出健全的人格,所以他提倡體育運動。早在1926年梅貽琦擔任清華學校教務長時,就規定體育課不及格的學生不得畢業。但他不贊成具有危險性的高難度運動,因為學生畢竟不是專業運動員。1934年,他對自己的學生說:今天我們提倡體育,不僅是為了鍛煉個人的身體,更是為了養成團結合作的精神。我們要借團體項目,去練習“捨己從人,因公忘私”的習慣。體育比賽的目的不在於能不能取勝,而在於是不是各盡其能,使本隊團結合作的精神得到有效表現。在體育比賽中,“勝固大佳,敗亦無愧。” 他的這一理念奠定了清華大學重視體育的基礎。
政治態度
在政治上,梅貽琦一直持守中間立場,他在日記中寫道:“余對政治無深研究,於共產主義亦無大認識。對於校局,則以為應追隨蔡孑民(元培)先生兼容並包之態度,以克盡學術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謂新舊,今之所謂左右,其在學校應均予以自由探討之機會。” 在長沙臨時大學期間,學校所請演講人中,各種人物都有,如共產黨領袖陳獨秀、湖南省主席張治中、國民黨高級將領陳誠等。在西南聯大八年歲月裏,沒有因政治原因開除過一個師生員工。校中既有聞一多、吳晗等進步人士;也有國民黨直屬區黨部,有三青團直屬西南聯大分部;此外還有地下黨組織,以及中國民主同盟等組織。對青年學子,他始終堅持不給他們灌輸任何政治派別的思想,而是培養他們個人的判斷能力,使他們依靠這種能力去決定自己的取舍與政治方向。在清華歷次學潮中,梅貽琦不分背景和黨派,無論是老師還是學生,只要遭遇到危險,就毫不猶豫地予以保護。1936年和1948年前後,國民黨政府曾數次到學校捉拿進步學生,每次在學校事先得到當事人名單後,立即設法通知學生躲避,這樣使許多學生免遭逮捕。
1948年12月13日,共產黨軍隊從清華門前通過,對北京形成包圍。12月21日,梅貽琦和另外一些學者乘坐國民黨派來的一架專機飛離了北京。國民黨政府再三邀請梅貽琦入閣,梅貽琦卻繼續堅持其一貫的中間立場,對新聞記者談話說:“不出來對南方朋友過意不去;來了就做官,對北方朋友不能交代。” 所以他始終婉拒,依然屬意於教育。1949年,他作為中國代表團主席參加了在巴黎舉行的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大會;同年12月,梅貽琦飛抵紐約,此後五年裏,他住在紐約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管理庚子賠款中國學生留美基金,用那筆錢資助了大約4000名在美沒有經濟保障的中國學生和學者。梅夫人則攜兒女於1951年1月從香港飛到紐約與他團聚。
儘管在北京和平解放前夕,清華師生們極力挽留,梅貽琦還是選擇了”出走”;儘管北京解放後,政務院總理周恩來曾對北大、清華兩校教授們說過:”梅貽琦先生可以回來嘛,他沒有做過對我們不利的事。”他還是留在了國外。據說有一次,可以無話不說的友人問梅貽琦,為什麽不留在中國大陸時,他說:我若留在大陸,只能有兩個結局:一是做”反革命”(指”右派”之類),一是做傀儡。這兩者都是我不願意的,所以只能離開。梅貽琦主持清華大學多年,能夠兼容左右,他很現實,雖不從事政治,但對政治認識得很清楚。他擁有理性和洞察歷史的先知先覺,他似乎預知到了什麽,因而也避免了什麽。
臺灣晚年生涯
1955年,梅貽琦被請回臺灣創建一個原子能科學研究所。他親自選址,指導建築設施,購置圖書和設備,並監督實驗室和廠房的建設工作。在新竹舉行的“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建成慶典上,教育部長這樣講道:“清華反應堆寫下了中華民國科學發展史上新的一頁,這也標誌著梅博士在獻身教育和科學上的最高成功。” 1956年,清華原子科學研究所更名為“國立清華大學”,梅貽琦再次擔負起校長的職責。他又一次發下真誠服務的誓言,同時也請全體教職員工和學生也都發下同樣誓言,贏得了又一代學生們的真誠愛戴和尊敬。
由於梅貽琦於1931年出任清華校長,直到他1962年在臺灣去世,一直服務於清華,因此被譽為清華的“終身校長”,受到所有清華人的崇敬與高度評價:“提到梅貽琦就意味著清華”,“梅貽琦是清華永遠的校長。” 因其一手奠定了臺灣清華的基礎,故又被稱之為“兩岸清華校長”。1959年,梅貽琦在臺灣被任命為教育部長,還兼任原子能委員會主任。當胡適博士擔任國家長期科學發展委員會主席時,梅貽琦又被任命為副主席,主持制訂《國家長期發展科學計劃綱領》的工作。
由於長期超負荷工作,簡食少眠,積勞成疾,1960年5月,梅貽琦因罹患骨癌入住臺大醫院治療。1961年2月獲準辭去教育部長職務;1962年2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同年5月又被任命為“國立中央大學”地球物理研究所籌備委員會主任委員。最後於1962年5月19日,梅貽琦因病情惡化在臺北去世,享年73歲。死後葬於新竹清華校園內,其墓園被稱為“梅園”,園內有校友集資栽植的花木,故又曰“梅林”。師生們每年都會到梅園向老校長獻花致敬,“梅貽琦紀念獎章”更成為該大學畢業生的最高榮譽。在北京,清華大學於1989年舉行了紀念梅貽琦誕辰100周年的紀念活動,海外清華校友贈送的梅貽琦半身銅像在此次活動中揭幕。
梅之遺屬
梅貽琦去世後十多年,梅夫人韓詠華一直在美國居住,其長女祖彬住在洛杉礬,三女祖杉住在費城。應周恩來之邀,韓詠華於1977年從美國回到北京定居,受到鄧穎超的熱情歡迎與接待,不久即被安排為全國政協委員。韓詠華於1993年8月逝世於北京,享年100歲。
梅貽琦和韓詠華共育有四女一子,即長女梅祖彬、次女梅祖彤、三女梅祖杉、獨子梅祖彥和小女梅祖芬。梅祖彥早年先後就讀於西南聯大和清華大學;1949年又畢業於父親梅貽琦的母校伍斯特理工學院;然後於1950年再赴伊利諾伊理工學院(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攻讀碩士學位。1954年3月,梅貽琦去臺灣開會,梅祖彥卻借道歐洲返回中國,沒料想父子倆紐約一別竟成永訣。梅祖彥回國後,一直在清華大學教授水力工程學,直到1998年退休。小女兒梅祖芬因當年在清華大學讀大二,未隨父母出國。五十年代初朝鮮戰爭爆發後,隨軍參加抗美援朝,後來在大連鐵道學院教書。
由於眾所周知的原因,梅祖彥一直不能與父親見面,直到1996年,他才得到機會到臺灣訪問,在新竹清華大學校長沈君山和張昌華老教授陪同下,到父親梅貽琦墓前行禮致哀,獻上遲到了34年(從梅貽琦1962年去世之日算起)的一束鮮花。
梅祖彥於2003年5月去世。2005年1月25日,在北京清華大學舉行的一個紀念儀式上,梅祖彥的遺孀,原北京大學教授劉自強女士將梅貽琦遺留下來的一幅畫、使用過的印章、家俱和一些照片捐贈給了清華大學。
資料來源
- 李可柔、畢樂思編著,單傳航等譯,《光與鹽——探索近代中國改革的十位歷史名人》。中國檔案出版社,2009年。
- 韓詠華,“我所了解的梅貽琦”,1981年。
- 梅祖彥,“懷念先父梅貽琦校長”,《永遠的清華園》。北京出版社,2000年。
- 《國立清華大學校刊》341號,1931年12月4日。
- 《國立清華大學校刊》第412號,1932年6月1日。
- 網絡相關資料。
關於作者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