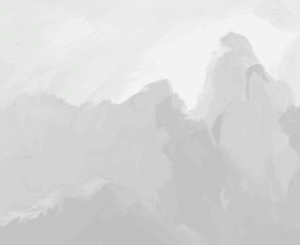早年背景
蘇達立(Stephen Douglas Sturton)於1896年9月12日出生在英國的劍橋。1904年,一個在中國醫療傳教的朋友來到蘇達立家中做客,並送給了小蘇達立一些中國禮品,向他講述了許多中國的故事。8歲的蘇達立由此開始對中國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並希望有朝一日也能成為一個傳教士去中國宣教。
1912年,蘇達立考入劍橋大學以馬內利學院(Emmanuel College, Cambridge)攻讀醫學學位;1918年畢業後在蘇塞克斯郡皇家海軍醫院任內科醫生。1920年,蘇達立遇到了一個在中國山東的醫療傳教士談起中國的情形,使他感覺到“神呼召我必須到中國做醫療宣教工作。”數個星期後他又遇見一位從杭州返英的醫療傳教士談起杭州廣濟醫院的情形,這個由英國聖公會創辦的醫院深深地吸引了他,於是他決定加入聖公會,請求赴杭州廣濟醫院工作。
杭州廣濟醫院歲月
1921年,蘇達立與從事護士工作的蘇安利小姐(Miss Rose Emily Jelley)結為伉儷,同年12月他們便為英國聖公會所派,一起前往杭州廣濟醫院工作。在1921-1926年期間,蘇達立和時任廣濟醫院院長的梅滕更(David Duncan Main)有過很多交集。1924年夏天,廣濟醫院莫干山臨時醫院開張後,蘇達立應梅滕更之請上山主理其事。為改善麻風病區環境,蘇立達爭取到英國國際麻風救濟會的援助,在新病區興建起磚木結構的男女麻風病房和隔離所、診療室和聖約翰禮拜堂,使醫院環境較前大為改觀,廣濟麻風病院一躍成為當時國內硬件設備最好的麻風病院之一。蘇達立還發展出一套以基督教信仰理念為基礎的麻風院管理制度。他認為:一個成功麻風病院運作的前提是“全體職員擁有基督信仰之體驗”,惟此才能更好地理解和實踐耶穌基督親身“潔淨麻風病人”之大義。
1927年,蘇達立回到英國利物浦大學從事熱帶病學的研究。1928年10月1日,蘇達立再次回到杭州廣濟醫院,並接任廣濟醫院院長。作為放射學專家,蘇達立還兼任醫院放射科主任,成為推動中國放射醫學發展的重要開創者之一。1932年10月4日,中華醫學會第九屆理事會學術大會在上海舉行,放射學專家首次以放射學組名義參會,蘇達立為首任放射學組(中華醫學會放射學分會的前身)主席。當時蘇達立領導的放射學組推動著中國早期放射學普及及臨床科研。不僅如此,蘇達立與同為杭州廣濟醫院的傅維德醫師合編了中國第一本放射學專業書籍《X光線引階》,1933年由中華醫學會出版,並於1949年由杭州新醫書局再版,改名為《X光學手冊》(A Handbook of Roentgenology)。
蘇達立一方面秉承老院長梅滕更的核心價值觀“顯仁”,致力於廣濟醫院的穩定與發展;另一方面發揚人道、博愛和奉獻的精神,參與人道救援的工作。
1937年,一場浩劫正在向杭州撲來,而蘇達立帶領下的廣濟醫院將在這場劫難中張開雙臂,勇敢地接受歷史所賦予的使命,與千千萬萬的中國人站在了一起。在那段黑暗的歲月裡,他們用自己的身軀為中國難民們帶來了一線光明。對於每一個接受庇護的中國人來說,他們就是生存的希望。
早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時,蘇達立就帶領廣濟醫院全體同仁全力醫治在空戰中受傷的杭州筧橋空軍將士。蔡廷鍇第十九路軍和張治中第五軍部隊的傷兵更是得到了廣濟醫院的全力救治,其中就有從杭州出征的著名的八十八師的官兵(該師一千余名犧牲英烈,後來葬於杭州松木場陸軍公墓)。蘇達立為此獲得了中國國民政府頒發的榮譽勳章。
1937年7月,蘇達立正在莫干山開診問病時,從收音機中聽到了“盧溝橋事變”的消息,便馬上下山,趕回杭州的廣濟醫院。一個月後,戰事蔓延到了杭州。1937年8月14日,蘇達立親眼見證了發生在杭州城上空的“八一四空戰”。那天下午4點,他正在和聖公會浙江教區高德斯主教(John Curtis)在閘口的亞細亞火油公司跟魏烈思(Frank Willis)經理一起享用下午茶,享受著片刻間的歲月靜好。忽然間,空襲警報聲響起,日本轟炸機空襲杭州筧橋空軍基地。蘇達立接到醫院電話後,急忙和高德斯一起返回城裡。途中,他們看到日本重型轟炸機飛越錢塘江上空以及炸彈爆炸的情景,還有數架中國空軍戰鬥機的驚險追擊。空軍英雄高志航打下日機後,自己也右手中彈,被急送廣濟醫院救治。據蘇達立自傳和報告稱,在隨後的四個月裡,杭州總共遭受到多達251次空襲,僅第一周就有9次空襲,整座城市被炸得千瘡百孔,而廣濟醫院則成為抵禦空襲的堅強後盾之一。同時在淞滬會戰中浴血負傷的官兵也陸續送達,第一批本來預計是35名重傷者,結果實際為60人,救治難度也相當大。廣濟醫院擴充了床位,所有人手都動員起來參與救治工作。社會各界也迅速行動起來,其他教會醫院和學校,以及佛教的寺廟都騰出場地用於救治傷員,最大的臨時醫院設在了千年古刹靈隱寺,整個杭州幾個星期內就收治了上萬名傷兵。按照國際法,教會醫院可以在紅十字會的名義下救治傷兵,由於廣濟醫院為英國教會所創辦,因此稱得上是杭州城中一個重要的“庇護所”。
1937年11月,淞滬會戰進入尾聲,有萬名傷兵被轉到杭州市內以及周邊,其中9000人可以撤退到後方,但有1000名重傷兵不能移動。如果得不到有效地救護,他們在杭州淪陷後恐怕性命難保。11月15日,杭州市衛生處處長張信培來找蘇達立,請求廣濟醫院接收一千多名無法轉移的重傷官兵,並許諾將鄰近廣濟的官立學校校舍劃撥醫院使用,並撥付一些必需款項。
當時,廣濟醫院的財政已經非常拮据,蘇達立隨後拜訪了當時的杭州市長周象賢商討此事。當周市長得知蘇達立表示願意接受這批重傷員後,立即支付一張國幣5萬元的支票,作為籌設重傷兵分院的費用。幾乎在同時,蘇達立又從倫敦市長支援中國基金申請到了每月的定期資助,財政問題暫告解決。最後,蘇達立和醫院同仁慎重選擇了無法撤退的重傷官兵共計660人,並於11月22日在寒冷的淒風苦雨中將他們轉移到重傷分院,交由蘇達立夫人及其助理人員負責照料。到12月23日,據蘇達立所記:“傷兵也儘量運送離開,最後就剩下重傷不能移動者202人。”
11月初,日軍在杭州灣登陸後,所有人都意識到杭州的陷落將不可避免,接著就開啟了持續數周的全城大逃亡,80萬人口最後只剩下10萬人,留下的大多是真正的老杭州人。面對殘暴的日軍,眾多百姓的命運將如何?廣濟醫院的那些傷兵又該怎麼辦呢?
杭州即將淪陷時,蘇達立是有機會撤離的,國民政府準備了專車供英美法等國人士離開,但蘇達立出於基督徒的愛心和醫生的責任心,以及紅十字會的理念,堅持留在廣濟醫院。在他的影響下,廣濟醫院大多數人都決心留下來。他說:“我們的首要任務就是設立難民營,以便於戰爭迫近時民眾能夠獲得逃難庇護。”
杭州淪陷後,在最恐怖的歲月中,蘇達立領導下的廣濟醫院為杭州百姓提供了一個生命的避難所。在1937-1942年間,他帶領著廣濟醫院的醫務人員,救助了千萬中國百姓和傷兵,而他自己最後卻被關進了日軍的集中營。
1937年12月24日聖誕節前夕,杭州淪陷,隨即從天堂跌落到地獄。當日上午,日軍殺進杭州城,其中包括惡名昭彰的號稱“菊部隊”的第十八師團,該師團剛剛參與了南京大屠殺,如今又給杭州帶來了空前慘痛的劫難。蘇達立在日記中寫道:“聖誕節中午,日軍開始大規模佔據杭州的房屋,傍晚沖進民房肆意掠奪,杭州慘遭恐怖統治的序幕被拉開。全杭州市90%被劫掠,許多婦女慘遭淩辱,12歲到60歲之婦女在此時都失去安全感。時常有受害婦女被送進醫院治療。另一種駭人聽聞的事件是日軍放火燒屋,數處火警都很靠近醫院。”聖誕節,這個本應充滿和平與友善的節日,對於當時的杭州百姓來說,卻成了苦難的開始。
據蘇達立回憶,有一天早晨,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朱孔陽來到我這裡。他說:“如果我們能夠救杭州免受巷戰,將是一件好事。”我說:“那當然,但怎樣才能辦到?”朱總幹事提議,由我發起,邀請高德斯主教、仁愛醫院的梅占魁主教(Bishop Georges Deymier)及長老會的麥穆蘭牧師,另有郵務司寇頓先生、亞洲煤油公司經理魏烈思先生,還有商會會長,一起到我家開會,商量具體事宜。”最後會議決定:向中國守軍司令部、並經由英國、法國及美國駐上海總領事向日方發出請求書,懇請體念傷兵、難民,並顧及天然美景和傳統文物,希望能避免在杭州市區內作戰。慶幸的是,該請求書獲得中日雙方軍事當局的同意。
在這次會議上,蘇達立和朱孔陽、田浩征、美國長老會的萬克禮牧師(Kepler V. Evera)、聖公會高德斯主教、羅馬天主教梅占魁主教、仁愛醫院院長彭姆姆、蕙蘭中學代校長葛烈騰牧師(Edward Clayton)等人,偕同杭州各界人士聯合成立了救援會,並推選蘇達立任紅十字會秘書長。當時的紅十字會會員包括中、英、美、法各國人士。救援會成立之初的當務之急是設立難民營。他們將平民傷病員集中到了天主教仁愛醫院,受傷的軍事人員和聯絡總部都放在廣濟醫院,救濟營建在各個教會場所、基督教青年會及西湖邊的瑪瑙寺等地,應急口糧則由商會提供。12月23日,救援會決定正式開放難民營。 難民營中懸掛起英、美、法等各國國旗及紅十字會會旗。在極度恐怖中,有17,000多名婦女、兒童和老人湧進難民營,尋求這些旗幟的庇護。由於蘇達立和其他傳教士多屬英美人士,而當時英美和日本並非交戰國,所以他們可以在難民營懸掛英、美、法等各國國旗及紅十字會會旗,以保護難民。
在蘇達立的自傳《從教會醫院到集中營》裡,通過他耳聞目睹的親身經歷,記錄下日軍所犯下的累累罪行,向全世界揭露他們的野蠻和嗜殺。日軍殺入杭州城後,到處都是哭喊聲和求救聲,蘇達立帶著紅十字救護車,奔走於杭州街頭,到處救死扶傷,利用自己的身份搶救下很多中國人,即使面對日本侵略軍也毫不退縮。
作為紅十字會的秘書長,蘇達立不僅親自醫治、救助了許多傷兵,還率紅十字醫療隊深入喬司等被日軍屠殺的地區。他發現在沒有外僑居住的小村鎮,日軍完全像野獸一樣殘忍,肆無忌憚地屠殺中國百姓,甚至毫不掩飾他們的罪行,只留下滿地的死屍和廢墟。在其自傳中,蘇達立記載道:“我經常以紅十字會秘書長的身份巡視市郊小村鎮。這些村鎮沒有外僑居住,情況比市區裡更淒慘。1938年初,我組織小組救援隊前往,……此時,閘口已是無人地帶,只見到處是遺棄的屍體,因無人收屍而臭氣熏天。有的剛被槍彈射死不久,仍浸在血泊中,也有無頭屍體仍保持跪下姿勢,有被砍頭而未全斷,背部被劈開的……其恐怖淒慘狀我有生以來從未見過。”
有一次在杜橋,蘇達立救出遭受日軍大炮轟擊的村民33人;第二天又從大火中救出數位婦女。在另一個村子,蘇達立和醫院員工與日本兵遭遇,出示紅十字會證件後仍被日軍帶到部隊檢查核准後才被放行,此行又救出23人。
英國著名記者田伯烈在其《外人眼中的日軍暴行》一書中,也記錄了蘇達立幫助難民的一些細節:“蘇達立暫時放下醫院院內的工作,專門負責外面救護難民的事情,醫院裡的汽車和救護車歸他使用。……在中國最動盪、杭州最恐怖的歲月中,他把更多的時間和精力投入到救難工作中,對第二故鄉杭州百姓的救助、傷兵的醫治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為防止日軍進犯醫院和外僑住宅,蘇達立在醫院裡組織了巡邏隊,由高德斯主教帶隊,郝惠琴(P. Haddow)和賈義德(M. Garnett)兩位女醫師輪流把守大門。他們還進行了一些基本的訓練以躲閃日軍的刺刀。
然而,在1938年還是發生了不幸的事件,就是“傷兵遭到日軍的逮捕和羈押”。當年 7月30日日本憲兵悍然闖入廣濟醫院,並在四周架設機關槍,共捕走103名痊癒期傷兵。儘管蘇達立和醫院全體員工奮力辯爭,僵持六小時,也無濟於事。日方企圖迫使蘇達立簽署移交文書,蘇達立寧死不從,他在後來給宣教會的報告中說:“我告訴日方人員:‘即使置我於死地,我也不會退讓半步’”。後來,蘇達立他們商定由高斯德主教前往上海向英國總領事彙報,並通過英國廣播公司、路透社等媒體將日軍的無恥行徑公諸於世。在外交和輿論壓力下,為緩和各方譴責,日軍當局同意蘇達立等人可以定期探視診療羈押在陸軍監獄的傷兵們。監獄的條件十分惡劣,擁擠而潮濕,每次蘇達立他們都是在日軍的刺刀下給傷員看病的。他們也給這些被羈押的傷兵帶去食物、信件等。經過不斷交涉,日軍在1938年11月3日明治天皇生日那天釋放了其中44人,另外59人被轉移到上海關押。醫院剩下最後一批傷兵於1939年的復活節順利出院,醫院還為他們舉行了歡送會。
自杭州淪陷至 1939 年之間,蘇達立聯手杭州著名律師田浩征等人,醫治了中國傷兵1000多人。廣濟醫院1938年總病例人數為88,000,超過戰前最高峰1926年的60,000人,蘇達立在1939年一份報告中預估當年會突破100,000例。除廣濟醫院外,還有基督教蕙蘭中學、仁愛醫院、弘道女中及青年會等地作為避難所,總共接納了25,000多名婦女和兒童。
幸好由於廣濟醫院的特殊背景還能維持,能收到外界的援助。蘇達立新申請了“美國諮詢委員會”的款項和“美國紅十字會”的醫療用品,“中華全國基督教協進會”所屬兒童基金專門資助營區的2000名兒童。蘇達立在一份寫給倫敦的通訊中寫到,他們曾在一個月內收到美國紅十字會的98病例的醫療用品、大量罐裝牛奶和鹹牛肉以及5噸麥片。這些物品的包裝袋上寫著“美國人民贈予中國人民”。
到1939年夏,難民數量已大為減少,傷員救治工作也暫告結束後,蘇達立夫婦啟程回英國休假探親,醫院暫由郝惠琴醫生任代理院長。兩個月後,蘇達立把夫人留在英國陪同兩個女兒,自己則幾經周折回到了廣濟醫院。可是回來後不久即因蚊蟲叮咬而患了血中毒,不得不臥床休息四個月。但他尚未完全痊癒,即投入到救難工作中去。
1941年12月8日,日本對英國和美國宣戰,將其佔領區內西方人統統視為敵人。當日上午,蘇達立正在醫院教堂做禮拜,從外籍同事口中得知日本向英美宣戰的消息。中午時分,駐杭日軍即派憲兵到醫院進行了搜查,沒收了無線電和一些“違禁”書刊,加派了監視哨,蘇達立他們與外界聯繫幾乎中斷了。傍晚,日軍突然闖入廣濟醫院,稱“你們仍有自由,但是我們要執行任務,逐屋搜查”。此後,醫院的院務雖然能夠繼續維持,但處在日本憲兵隨時“監視搜查”中。8月31日,日軍突然下令要徵用廣濟醫院以醫治他們的傷兵,逼迫蘇達立將醫院移交給日本軍事醫務機關。
1942年11月11日,蘇達立因為“幫助治療中國傷兵”之罪名,被四名日軍憲兵拘捕,第二天就被押送到上海海防路集中營監禁。集中營內關押了英、美、丹麥、比利時、希臘等國的360名外僑,年齡最小者21歲,最大者已74歲。日軍視他們為“危險的戰犯”,讓他們忍飢挨餓,受盡淩辱。蘇達立記載:“營犯中時常有人隨時被憲兵提到總部詰問或被特別拘禁,時間從24小時到3個月不等。各國男女混雜,擁擠污穢,受盡淩辱和饑餓。”
1945年6月底,蘇達立與其他外僑被日軍強行“轉移”到北京郊區豐台一個“在日軍嚴密軍事管制防衛,甚至連日軍士兵都不允許閱讀任何報紙”的集中營,直到日本宣告投降後才獲釋。
抗戰勝利後,蘇達立重獲自由並再次擔任廣濟醫院的院長兼麻風病院院長,繼續為杭州市民服務。經過幾年的努力,杭州廣濟麻風院的聲譽又逐漸傳遍全國。1948年,鑒於麻風治療住院的病人日漸增多,蘇達立與醫務部主任馬雅各一起籌劃麻風病院擴大事宜。1949年在武康上柏的鴻漸嶺創辦了國內最早的“麻風村”形式的農場。
離華赴港
1951年,蘇達立等聖公會有關負責人,將廣濟醫院估價舊幣32多萬元,租給浙江醫院作為教學醫院。同年,蘇達立等外籍醫生回國。離開杭州前,他和昔日戰友田浩征律師一起騎著自行車來到錢塘江邊,站在錢塘江大橋上,最後一次注視著這座他曾經生活與工作30年並為之付出一切的城市,深情地與她道別。這個曾在風雨如晦的時刻守護著杭州的醫療傳教士,帶著對中國人的愛,帶著心靈的創傷和苦痛回到了他自己的祖國,卻留下一座歷經風雨滄桑的醫院,依舊矗立在杭州這片土地上。
蘇達立雖然身返英國,心裡卻始終牽掛著中國人民。不久,他又到香港行醫,直到力盡方休。1970年9月28日,這位忠於其信仰與使命,深愛中國百姓,並在危難中拯救千萬生命的“杭州的拉貝”,在英國黛芳的布朗頓(Braunton, Devon)辭世,享年74歲。
資料來源
- Stephen Douglas Sturton, From mission hospital to concentration camp.(蘇達立回憶錄《從教會醫院到集中營》)Marshall, Morgan & Scott, 1948.
- 蘇達立,《1937-1942腥風血雨杭州城》。
- 田伯烈著,《外人眼中的日軍暴行》。
- 英國伯明翰大學圖書館特藏部有關英國聖公會杭州廣濟醫院檔案資料。
- 史偉東、羅巍編著,《苦海方舟濟蒼生——蘇達立、明思德與杭州抗戰救難》。杭州出版社,2021年。
- 多源焦點,“蘇達立與杭州抗戰救難”(上、下)。原文網址:https://kk-news.cc/news-food/15e5a9.html
- 侯小勇的尋訪傳教士的足跡,“蘇達立|被譽為“杭州拉貝”的醫療傳教士”。
- 網絡相關資料。
關於作者
作為世華中國研究中心的資深研究員,李亞丁博士現擔任《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inese Christianity) 的執行主任和主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