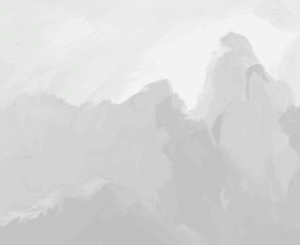天主教耶穌會意大利籍傳教士、科學家;利瑪竇(Matteo Ricci)的親密同修和助手。1606年來華,到北京傳教,並任職於欽天監,修訂歷法,著作等身。
一、早年經歷
熊三拔(Sabbatino de Ursis)的名字Sabbatino 是來自他的祖父Sabbatino III(薩巴蒂諾三世)聖班奈迪克伯爵。據他的家譜記載,薩巴蒂諾三世的女兒Concepta, 和一位來自阿普利亞的紳士結了婚,他就是熊三拔的父親。薩巴蒂尼家族當時極為看重這樁婚事,他們給新生的男嬰命名Sabbatino,來紀念他的祖父。
薩巴蒂諾在歷史上是一個顯赫的姓氏,這個家族和利瑪竇的家族一樣,和梵蒂岡有著密切的聯系,熊三拔的成長故事和利瑪竇也非常相似。熊三拔的童年生活與教堂息息相關,他人生的第一課就是天主教的宗教信仰。熊三拔最喜歡閱讀的書是《兩種命運(好運和厄運)的補救方法》(De Remediis Utrivsque Fortunae)。該書在文藝復興時期及之後,是許多漂泊各地之遊子們手中不可或缺的“寶書”。這本書於1515年在威尼斯出版,是獻給洛雷托市(Loreto)執政主教的禮物。洛雷托市是歐洲各地虔誠基督徒們朝聖的目的地之一,也是利瑪竇當初信仰形成和建立世界觀的“聖地”,它對利瑪竇人生道路的選擇影響巨大。數十年後,它也深深地影響了年輕的熊三拔的人生態度與人生方向。
二、熊三拔和利瑪竇、徐光啟
熊三拔少年時便離開了家鄉阿普利亞,1597年來到羅馬就讀耶穌會學院。30年前,利瑪竇也在此求學並汲取了大量的知識。1606年,熊三拔隨郭居靜(Lararus Cattaneo)到中國澳門,及至南昌,並被派至北京與利瑪竇相識。當熊三拔初抵中國時,利瑪竇已經在中國生活十余年了。熊三拔的年紀比利瑪竇小24歲,一到中國就立即被分配協助利瑪竇從事傳教活動。熊三拔當時在某些學科領域的知識量已是相當驚人了,但與利瑪竇相比還是“小巫見大巫”。利瑪竇是一位真正的“百科全書”式的學者,幾乎通曉當時所有藝術科學,而熊三拔則偏向於精通某些科技領域的知識,擅長農業學,尤其是水力學。當時,耶穌會學院的教育方針是,越是年輕、有才華的學生,越會在主要的學科領域得到高質量的教育。利瑪竇在天文學和幾何學上的造詣出色;而熊三拔則在機械學、水力學、應用科學等科目獲得了更多的知識。
熊三拔在求學期間取得了優異的成績,並且對繼承先人到遠東傳教表現出了濃厚的興趣,因此他來到了中國,當時利瑪竇和徐光啟一起剛剛完成了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的翻譯工作。熊三拔一到北京,立即加入到《幾何原本》譯本的第一版校訂工作。與此同時,在對數學、天文學、應用科學等專業用語進行漢化的過程中,熊三拔也從利瑪竇和徐光啟那裏學到了大量的知識,累積了豐富的經驗。他一直追隨這兩位偉大的學者,直到1610年利瑪竇逝世。
利瑪竇對熊三拔有著一份特殊的感情,並視其為他最為鐘愛的學生。他將熊三拔推薦給徐光啟,並在晚年時,自覺時日無多,還托囑徐光啟要好好照顧熊三拔,稱贊熊三拔是當時眾多耶穌會士中最有前途的人,並且建議徐光啟讓熊三拔來完成接下來的歐幾里得眾多著作的翻譯工作。
在熊三拔和利瑪竇兩人的關係中,還有一層是特別重要的,那就是他們互為對方的懺悔者。依照天主教教義,神父在被賦予傾聽眾生告解的權力時,其自身也必須定期向另外的神父告解,以審視自己的行為。所以,在中國傳教期間,熊三拔和利瑪竇兩人朝夕相處,恪守並監督彼此的日常行為,在遇到困難時,相互勉勵。若其中一人認為另一人的行為違背了忠誠和善行,抑或是做了某些不當之舉,他們會馬上進行告解。在利瑪竇臨終前的日子,熊三拔是它最重要的助手,兩人結下了深厚的友誼並相互尊重。1610年5月10日,在完成人生的最後一次告解後,利瑪竇在熊三拔的懷中溘然而逝。利瑪竇去世前,把最重要的文件資料都移交給了熊三拔,並告訴熊三拔他最大的遺憾是雖然身在北京,卻沒有見到被他稱為“東方康士坦丁大帝”的萬曆皇帝,沒有使他皈依基督教。
三、熊三拔的主要成就
利瑪竇去世後,熊三拔繼承其遺志,對《幾何原本》的翻譯工作進行了最後的完善和校正。此外,他也和農業知識淵博的徐光啟一起,對中國境內的主要水係,尤其是上海、南京一帶的河流分佈走向制定了周詳的設計方案,按照他們的設計而興修的大部分水利樞紐和運河系統至今仍保存完好。熊三拔繼續與徐光啟合作,譯著了多本著作,而且在許多科技領域的研究方面不斷有新的突破。
熊三拔在中國傳教約15年,共留下《泰西水法》、《簡平儀說》、《表度說》、《中國俗禮簡評》和《陸若漢神父著述註解》五本書,以及一些關於教義和傳教經歷的信劄等。《泰西水法》、《簡平儀說》、《表度說》等,均被收入《四庫全書》,其中第一部還被徐光啟收入《農政全書》。《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是中國古典目錄學的集大成,體例最完善,影響最大;《農政全書》是對傳統農學的總結。
《泰西水法》一書共六卷,是集歐洲古典水力工程學之精華,是傳入中國的第一部介紹西方農田水力技術的著作,主要介紹西方取水、蓄水、運用水力之法,並以圖伴文,1612年在北京刊行。因水利有關農業灌溉,所以後來徐光啟著《農政全書》時,其水利部分曾抄錄此書。後來清代初年的宮庭建築,如圓明園的噴水他,亦系採用西洋水法,並為西洋傳教士所督造。《泰西水法》除講水力外,還附以治病之藥露。清初西方的藥物學傳到中國並且很快地為中國人醫病所採用。熊三拔著有《藥露說》一卷,並附有蒸餾及制造藥爐等儀器的圖說。
明清之際,西方天文曆算之學大量地輸入中國,此舉起於“修明曆法”的需要。中國天文曆法雖然歷史悠久,但是到了明末,由於當時實行的“大統曆”、“回回曆”,年久失修,推測交食多不相合,改曆之議隨之而起。恰在此時,利瑪竇等人向中國介紹了西方先進的天文學和曆法。他於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翻譯《乾坤體儀器》,首先介紹了有關日月蝕的原理、七曜與地球的比較、西方已測知的恒星,以及天文觀測儀器的制造等。同時,他還向中國人介紹了制作渾天儀,地球儀、考時晷等天文儀器,這是西方天文學傳入中國之始。繼利瑪竇之後,熊三拔等人共同參加修曆,比較在歐洲、印度和中國推算日蝕結果,測定從廣州至北京的緯度。熊三拔所著《簡平儀說》和《表度說》詳細介紹了簡平儀的用法以及根據天文學原理測日定時的方法。他還和徐光啟、李之藻等共同翻譯西方曆書多種。
四、悲劇性結局
意料不及的是,1609年,耶穌會士龍華民(Niccolo Longobardi)被招至北京,擔任在華耶穌會全國會督。在編纂《洗禮用語》一書上,其意見與利瑪竇不同,以致引起後來的禮儀問題,並在教會內部掀起極大的分歧和爭論,使得耶穌會在華的處境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自利瑪竇以來,許多耶穌會士對中國天主教徒遵循儒家傳統跪拜祖先的禮儀采取的是寬容的態度,但其他修會,如道明會和方濟會的傳教士對此則持有更為嚴格的態度,因此產生了矛盾,導致梵蒂岡教皇親自頒布禁令,不允許中國的教徒跪拜祖先。此舉激怒了康熙皇帝,使他改變以往的寬容態度。繼康熙之後的雍正皇帝更加反對天主教,甚至發布聖旨,驅逐所有在華的外國傳教士,其罪名是幹涉中華文化傳統和朝廷內政。
1616年(萬曆四十四年)從5月至12月,南京禮部侍郎沈漼以治曆問題和祭祖問題為重要理由,連上三道奏疏,參劾耶穌會傳教士,在南京發動仇教運動。7月沈漼在南京逮捕了王豐肅(Alphonsus Vagnoni)和謝務䘵(Alvarus de Semedo)兩名外國教士和十幾名中國信徒。8月初,在北京的龐迪我(Diego de Pantoja)和熊三拔等11名傳教士也被逮捕,關在木籠裏,於1617年被解送到南京,續由南京解往廣州和澳門。1620年,顛沛流離的熊三拔在澳門病逝,年僅45歲。冥冥中似有天意,熊三拔一生經歷似乎和他年少時最愛讀的《兩種命運(好運和厄運)的補救方法》一書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令人扼腕嘆息。
熊三拔的遺體留在澳門,但他的名字卻和利瑪竇的名字一起列在了位於北京西城區車公莊大街明清天主教傳教士的紀念墓地(滕公柵欄墓地)裏。利瑪竇、湯若望等對中西文化交流有著重大貢獻的許多傳教士都葬在這裏。惜在1900年義和團之亂中,所有外國傳教士的遺骸都被挖出並隨意丟棄,最終無人能夠分辨這些遺骨究竟歸屬何人。
熊三拔的事跡和成就在他的後裔中一直流傳至今,而倪波路(Paolo Sabbatini)就是其後裔中的一位。值得告慰的是,400年後的1999年11月,徐光啟後代徐承熙、利瑪竇家族後裔路易吉·利奇(Luigi Ricci)應邀到倪波路在上海的寓所中相聚,暢敘往昔蹉跎歲月。
歸屬
This article is reproduced, with permission, from A Dictionary of Asian Christianity, copyright © 2001 by Scott W. Sunquist,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Grand Rapids, Michigan. All rights reserved.
資料來源
- 倪波路著,《我先祖的故事:利瑪竇、徐光啟和熊三拔》,浙江大學出版社, 2010年。
- 呂元驄、葛榮晉著,《清代社會與實學》,香港大學出版社,2000年,152頁。
- 陳健夫著,《基督教在華早期傳播史》。浸信會出版部,1972年。
- 王治心著,《中國基督教史綱》。基督教文藝出版社,1993年。
- 網絡相關資料。
關於作者
作者係美國加州基督工人神學院碩士研究生,在李亞丁教授指導下撰寫此文。